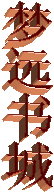
林斤澜文集 姐妹
李婕和李媚大概不是亲姐妹,他们都不记得父母亲的面貌了。李媚连怎样到的保育院也记不起来,后来就把李婕的经历当作自己的故事。其实李婕也只记得一点点影子:那天,家里有人叫她上街打酱油,提着瓶子回家时,警报机鬼哭一般嚎了起来。立刻来了日本飞机,投弹、放机枪,身边的房子着了火,有人把她挟在胳肢窝底下乱跑。后来给送进一家临时保育院,和李媚一起,落到一个油黑油黑的胖保姆手里。胖保姆每天指使孩子们喂鸡、洗衣服、劈木柴,没有做完这样又叫做那样,时不时地,油黑的手指头拧住孩子们的皮肉,还转它几转,跟拧螺丝钉差不多。李媚一天不知哭多少遍,但每遍都是抽搭几下就过去了,眼泪未干,就唱起只学会一句的歌子: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李婕不哭也不唱,眼睛睁得大大的,冷淡地、固执地做着做不完的事情。可她也不少挨拧,因为她有一种拗脾气。比方正在扫地,胖保姆叫她去抱木柴,她却管自把地扫利落了。刚抱起木柴,又叫她提水,她总是把木柴抱完再说。
李婕有时拿小拳头吓唬李媚:
“哭死鬼,再哭我也要捶你了。”
有时搂着李媚说:
“有哭的工夫,你不会思办法对付她。”
这样,李婕做了李媚的姐姐。大约过了两回年,日本人打过来了,保育院站不住了,把姐妹两个送给大后方的一个战时学校。名单上写的是李姐、李妹,学校的教员一摇笔杆,改成李婕和李媚。
这学校是一位民主的教育家办的,分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组,让孩子们从小就受专业训练。并且让一张白纸似的孩子们自由选择,任性发展。几年工夫,姐妹两个却把几个组都走遍了。头一年学的是美术,李媚抓铅笔、抓炭条,画了许多歪脖子的花瓶、窝窝头似的山景。一年工夫,就会画半边黑半边白的人脸了。李婕的画还要整齐一些,可是她说:
“妹,你怎么知道你画画顶合适呢?”
“姐,画画你还不喜欢吗?我可是画一辈子也不厌,明年还让我们用颜色了呢!”
“咱们转到戏剧组去吧。长大了演戏、拍电影,比什么都好。”
“姐,画画不也挺好。”
“我想着我们两个好像生下来就在一起的,可是现在要分开了,反正我是要到戏剧组去的。”
“姐,那我也去吧。”
姐妹两个在戏剧组呆了半年,排了一出戏。姐姐演个小学生,妹妹演一只小白兔。姐姐是主角,妹妹跑龙套。排演的成绩都不错,可是演出那天,姐姐生了一场气,妹妹大哭了一场。原来小学生这个主角,是AB制的。导演派别人上台,让李婕在后台管提词。李婕把台词本子一扔,冷笑道:
“早知道会是这样的。”
导演向她解释AB制,李婕瞪大眼睛,有条有理地说道:
“别解释理由还好些哩!要说理由,我演得比谁差吗?为什么我是B?我要演得不好,排演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不教?难道非得天天晚上找你玩儿,才算得好学生?”
弄得导演答不上来,孩子们都吓呆了。妹妹糊里糊涂穿上小白兔的服装,上了台,看见小黄兔叫狼咬坏了,就伤心大哭。哭得说不上台词,全场鼓掌。
演完戏,李婕说:
“妹,上舞蹈组去。演戏没有意思,有多大的本事,也要看导演的脸子。”
“姐,还是演戏好,这么多人在一间屋子里,一块哭一块笑。我喜欢演戏。”
“演戏不如舞蹈。你没听说全国还没有办过舞蹈班?我们去了就是第一批。”
姐妹两个忽然都十四五岁了,忽然长成苗条的少女。仿佛水仙花,觉着还是一块球根,一不留神,长得绿油油,水灵灵。姐妹两个身边,都有一群男孩子。姐姐爱挑,挑一个随着玩随着上街,过几个月另挑一个随着。妹妹是谁对她好,她就跟谁玩,常常一个晚上跟这个散散步,跟那个唱唱歌,又应约跟别人看月亮去了。男孩子们有时闹意见,她就躲到一边抹眼泪。李婕教训她:
“哭有什么用呢!有哭的工夫,你不会想办法对付他们。”
李婕身上有了许多精致的小东西,有时塞一条挑花手绢给李媚:
“妹,拿去。”
一双毛绒手套:
“妹,给你。”
一条纱巾:
“妹,围上。”
姐妹两个最后转到音乐组。李婕说:
“妹,我主科学唱,你主科钢琴。我唱歌,你弹伴奏,我们就一辈子在一起了。”
音乐组里有位声乐教员,年轻潇洒。当他虚着眼神,一只手掌托在耳朵后面,还没有发声,那派头就是很艺术的。第一天上课,他就十分欣赏姐妹两个的声音:
“小提琴,简直是小提琴。多么好的本钱。”
过不了多久,就格外加钟点个别上课,还请她们吃U.S.A.的巧克力。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教员跟姐妹两个看了好莱坞的《出水芙蓉》回来,走上黑暗的楼梯,李媚的一只手,叫火热的男人的手捏住了。李媚心跳,活像有个迷路的小鹿儿在里边乱撞。转弯时,踩虚了一脚,有只男人的胳臂搂住她的腰。李媚朦胧听见说:“明天一早逛公园去。”就昏头昏脑走进寝室,想说:啊呀吓坏了人,这不是恋爱了吗?可是第二大醒得晚了些,起来一看,静悄悄的,都玩儿去了。赶紧往公园里跑,却在树缝中间,看见教员和姐姐挨着坐在草地上,不觉惊叫了一声。
晚上,李婕钻到李媚床上。
“妹,别装睡了。”
“嗯。”
“妹,你喜欢他了。”
“啊,姐,啊,你怎么知道的?”
“早看出来了。可我也喜欢他,比你还早。”
“姐,过一阵子你又会不理人家了的。”
“不会,这一回是真的。你摸摸,我从来没有这么心跳过。”
“要是真的,我就不难过了。”
往后李媚真的不怎么难过。只是声乐课再也不能上了,专练钢琴。休息的时候躲着姐姐,最好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上哪儿玩去了。到了第二个学期,忽然李婕跟一个新来的教员练声了,跟别人去看电影了。
“妹,你别瞪着我。小傻瓜,你不是他的对手,怎么能让你跟他闹下去。”
“可你说这一回是真的。”
“起初倒像真的。可是有一天练声,那家伙说摸摸我的气,越摸越往上去。我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妹,要是你,怎么对付得了,你会闹糟了的。”
“为什么不早说。”
“早说你肯信?妹,别走。那家伙声乐上有点本事,可是不好好教,谁也学不到东西。可是这学期,我进步了一大截。他那两下子我也学得差不多了,为什么不换个先生呢?……”
李媚没头没脑钻进被窝。她没有哭,只是身上发冷,上下牙直打战,仿佛疟疾发作了。这光景不象伤心,倒象吓坏了。
可是不久,这件事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日本投降,蒋政府却要打内战。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的运动风起云涌。姐妹两个的学校,走在运动的前头。开群众大会时,少年同学们总是手挽手站在台口,压住阵脚。有回一伙特务冲上台去,霸占主席台。台下群众喊着口号,潮水般往前推进。一个特务头目,站在台口指手画脚。李媚给人群挤到台边了,气得大喊大叫,拼命摇着手里的纸旗。忽然耳边听见李婕说话:
“妹,生气有什么用,想办法对付他。”
伸手就把旗纸撕下,剩下一条光竹竿,一下子捅进特务头目的裤脚管。
台上台下一阵大乱,李媚在人群里东挤西撞的喊口号。忽然一只手攥住她的胳臂,死命把她往外拽。拽出人群,才知道是姐姐。
“妹,站在这里看着。现在该是男孩子的事情了。”
李媚脸红气喘的瞪着主席台,觉得姐姐塞了一快东西在她手里。一看,是块花生糖。
“姐,哪来的糖?”
李婕伸手一指,笑道:
“你没看见那糖担子打翻了,卖糖的不知给挤到哪儿去了。”
蒋政府发动内战了。觉醒了的少年学生们,私下啾啾地商量一件大事。有天晚上,李媚拉着李婕找个清静角落说话。
“妹,就在这里说了吧。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到解放区去吗?”
“啊,姐,啊,你又知道了。”
“早看出来了。妹,我们两个好像生下来就在一起的,本来说什么也不愿意跟你分开。可你这样的人,在这里有危险。我想了又想,没有别的路子,你还是走吧。”
“姐,我要你一块去。”
“我不去。”
“为什么?”
“要是我三十岁了,也会去的。可我现在还没有生活个够。”
“到了那边,倒没有生活了吗?”
“那边是另外一个世界。”
“那你要的是什么生活呢?”
“你走你的吧,别管我了。”
姐妹两个生平第一次因为意见不同,互不相让。虽说没有吵闹,可是不欢而散。
李媚走后,李婕也离开了学校。这个剧社、那个剧团地混混,到处有人包围她追求她,可是总演不上一个出头露脸的好角色。李婕眼睛瞪得大大的,冷淡地、固执地应付人事。有回,一个名声很高的剧社,要一个女孩子扮演站在石座上的女神,要一动不动地站上个半钟头。李婕一笑应下这个角色。到上演时,她让导演同意一种服装,那是一片轻纱,里面只穿一点点衣服。立刻引起好些人的兴趣。有一家没有自己的摄影场的电影公司,找她拍一部片子。李婕答应了上镜头,还答应了导演的求婚。可是她刚刚穿上海勃绒大衣和尼龙丝袜,那家公司就破产了。
五六年后,全国解放了。一个文工团在城市里招考团员,李媚担任声乐考试。她坐在钢琴前面,眼角瞧见一个白白的瘦瘦的女演员,从背后走过来。李媚一哆嗦,叫道:
“姐!”打算扑过去。
可是李婕冷冷地走到钢琴旁边,固执地说道:
“妹,你考我吧。”
“姐,你唱个歌,我来伴奏。”
李媚长大了。她居然能够用这么句话,缓和千头万绪的新局面。可是被妹妹考试的事实,总叫李婕心酸。她无可奈何地进了文工团,眼睛睁得大大的,站在一边看着妹妹红了,得意了。一个是歌舞队队长,一个只是新来的普通团员。李媚知道李婕有了两个孩子,想上姐姐家看看,可是被冷冷谢绝了。李媚也已结婚,请李婕上家里玩玩,她也固执不去。李媚心想:她们已经不只是姐妹,还有队长和新团员的一层关系。曾见过几个新来的知识分子,总是冷冷地站在一边。最好不忙去碰他们,惊动他们。让他们熟悉熟悉,赶到适当的时候,使劲拽他们一把。李婕心想:妹妹有时也念旧情,有时又全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丫头学会了里一套外一套了哩!因此,两下里疏远了。
一个初冬的星期天,李媚上街看见姐姐在前面走,身边有两个孩子,衣服零乱,光脚穿着张了嘴的鞋子。李媚盯着那两双小脚,仿佛看见的是冻红了的小脚板,劈啪劈啪踩在水门汀上,心头涌上姐妹两个在保育院时的光景。猛然觉得自己太不关心姐姐了。可是远远跟了一条街,还是决定不上去打招呼。往后就从当时刚够维持生活的津贴费里,省下钱来买小鞋小袜,装做不经心地塞给李婕:
“姐,给孩子。”
“姐,拿着。”
李婕每回都是冷冷一笑,生硬收下。第一回李媚有些难受。第二回肯定了姐姐的感情很不对头。第三回又警觉到另外一面,姐姐不象有些新来的人:赶红火,凑热闹……
文工团排演新节目了。排的就是当时流行的从落后到转变的话剧。主角是一种思想类型,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导演要李媚扮演主角,李媚考虑了一晚上。第二天说:“有一个人比我合适。李婕。导演同志,你不用瞪眼珠子。我不愿意老做行政工作,我本来是个演员,我不愿意放过演主角的机会。一点也用不着推让,更没有理由让给姐姐。可是李婕能演好这个角色。她现在对集体还缺乏信心,我们要帮助她成为团体里边的好演员。导演,你别瞪眼。你心里在说,不能为了这个糟蹋演出。可是你想,要让搞艺术的,通过艺术实践改造思想,同时也提高了艺术。这种例子还少吗?爽直点说,你就是一个。”
说得导演哑口无言。
有天晚上排完戏,三九天气,可是李婕拿着手绢,扇着微微冒汗的红红的脸。没有见她这样兴奋过。
“姐,你演得很好。”
“要是恭喜我,还嫌早了一些。”
“姐,我想到一个问题。”
“我知道了。是不是转变的时候,不够自然?可是我真正没有法子了。”
“当然,转变那一场,剧本要负很大的责任。可是我说的是整个表演。对那些个人主义的东西,你好象不自觉地欣赏、玩味,好象没有批判,没有站得高一点。所以你演得虽说流利,但是不深厚。”
这个见解是李婕没有想到过的。一时琢磨不透,但已隐隐觉得这比自己高明。因此,脸上又透出冷冷的神色了。李媚见她刚刚有些热情,却立刻往回缩。就拉住姐姐的手,不想看见姐姐的鬓发中间,有块青伤。赶紧问怎么回事。
“家务事,打了一架。”
“姐,常打架吗?”
李婕一笑不语。
“啊,都为的什么呢?”
“自私!”李婕断然回道,“他自私,我自私,连孩子们也自私。”
“啊,姐,我不懂。”
“有什么不懂。都想少付出,多收入。”
“姐,这中间还有什么付出、什么收入的呢!”
李媚拉着李婕到自己家里去,怎么也要跟姐姐好好聊聊。半夜到的家。出乎李婕意外,那妹夫害着不时会发的气喘病,这回卧床已经二十来天了。李媚安置姐姐坐下,就来来去去砸煤、添火、提水、倒痰盂。病人把棉被盖到下巴,只露出一张微笑的瘦脸。可是李婕看见妹妹走出房间时,那微笑就不见了,还把棉被推开一些,呀,呼吸有些困难。最后还是叫李媚发觉了,赶紧找药针注射,可是药又没有了。李媚不管病人怎么说,一面笑着告诉姐姐这是常有的事,一面穿外衣戴帽子,钻到北风呼呼、黑咕隆咚的街上去了。
李婕等到下半夜一点多,却接到一个电话。妹妹问病人怎样了,说她敲遍了内城药房的门,有的不开,有的没有这种药。现在要上外城敲门去了。李婕接完电话,关上电灯,对着红红的炉火,把自己舒舒服服地埋在沙发里。她觉着妹妹的处境跟自己也差不多,并没有高多少级。憋在心里多时的紧张一下子消失了,她暖洋洋地睡着了。
惊醒时,看见李媚在轻脚轻手地点酒精灯,洗玻璃管。原来妹妹学会了注射。等到姐妹两个躺到床上时,已有赶早市的大车,隆隆滚过胡同。李婕对着精疲力尽、(足卷)缩在自己身边的李媚,觉得自己已回复到姐姐的地位。好兴致地叹道:
“妹,你也命苦啊!”
“命苦?什么意思?具体点说呢?”
“想不到你嫁了个长期病号。”
“他的病是叫敌人剥了衣服,扔在雪地里冻坏的。”
“你自己也要保重。常常半夜里满世界敲药房的门,你也会变成长期病号的。”
“姐,我着急啊。有回,交通警察把我当做疯子了呢。”
“着急有什么用,有着急的工夫,你不会想办法对付——处理……”
李媚吃了一惊,觉得这句话那么熟悉又那么疏远。想道:姐妹两个好像生下来就在一起的,不知怎么一步步离得这样远了。又忍住千头万绪,说:
“姐,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说。可是这忽儿脑子轰隆轰隆的,咱们睡一睡吧。最好早早醒来,象小时候那样,赖在被窝里小声说话,看着窗户一格子一格子地亮了,咱们越说越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