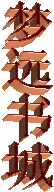
钟理和文选 假黎婆
一有一天,惯例在每年春分去下庄的大哥回来时告诉我说,他在下庄碰见奶奶
的兄弟,说是这位兄弟心中着实惦念我们,不久想来这里看看。这消息令我兴奋,
同时也带给我一份莫可名状的怅惘,和一份怀旧之情。
我这位奶奶并不是生我们父亲的嫡亲奶奶,而是我祖父的继室。我们那位嫡亲
奶奶死得很早。她没有在我们任何人之间留下一点印象,所以我们一提起“奶奶”
时,便总指着这位不是嫡亲的奶奶。事实,我们这位奶奶不仅在地位和名份上,就
是在感情上,也真正取代了我们那位不曾见过面的奶奶。我们称呼她“奶奶”,她
是受之无愧的。她用她的人种的方式疼爱我们、照料我们,特别是对我;她对我的
偏爱,时常引起别人的嫉羡。
她是“假黎”——山地人。我说用她的人种的方式,并不意味她爱我们有什么
缺陷或不曾尽职,只是说我们有时不能按所有奶奶们那样要求她讲民族性的故事和
童谣;她不能给我们讲说“牛郎织女”的故事,也不会教我们念“月光光,好种姜”,
但她却能够用别的东西来补偿,而这别种东西是那样的优美而珍贵,寻常不会得到
的。
据我所知,她从来不对我们孩子们说谎,她很少生过气,她的心境始终保持平
衡,她的脸孔平静、清明、恬适,看上去仿佛永远在笑,那是一种藏而不见的很深
的笑,这表情给人一种安详宁静之感。我只看到有一次她失去这种心境的平和。那
是当人们收割大冬稻子的时候,清早她到田里去捶谷,忽然人们发现她在稻田上跳
来跳去,一边大声惊叫,两手在空中乱挥乱舞,仿佛着了魔,后来竟放声哭将起来。
大家走前去。原来地面上满是蚯蚓在爬,多到每一脚都可以踩上七八条。她生平最
怕的是蚯蚓。我大姑姑笑得蹲下身子,但毕竟把她驮在背上背回家去。
她的个子很小,尖下巴,瘦瘦,有些黑,居常把头发编成辫子在头四周缠成所
谓“番婆头”,手腕和手背有刺得很好看的“花”(纹身)。我所以知道她是“假
黎”,是在我较大一点的时候,虽然如此,这发见对我并不具有任何意义。把她放
在这上面来看她、想她、评量她,不论在知识上或感情上我都是无法接受的,那会
弄混了我的头脑。我仅知道她是缠着番婆头,手上有刺花的奶奶,如此而已。我只
能由这上面来认识她、亲近她、记忆她!
二
我不知道我几时而且又是怎样跟上了我奶奶,我很想知道这事,所以时常求奶
奶讲给我听,碰着她高兴时,她会带着笑容一本正经的答应我的请求。那是这样的:
据说有一天大清早她要去河里洗衣服时,她看见一个福佬婆把孩子扔在竹头下,她
待福佬婆去远了就走前去把孩子抱起来,装进洗衣服的篮子里带回家去,这便是现
在的我。
后来,我长大了,我知道每一个做母亲的都要对自己的宝宝们解释她怎样的捡
起他们来,不过在她们的叙述中,那个扔孩子的女人都是“假黎婆”,而我奶奶则
把她换上了“福佬婆”(闽南女人)。
不同的只有这一点。
据我后来所听及推测,似乎是在我有了弟弟那年,开始跟上奶奶,那时我妈妈
怀里有了更小的弟弟,不能照顾我了。
不过又说那时我还要吃奶,那么怎么办呢?于是便由我奶奶用“炼乳”喂我。
那时候民间还不晓得用保暖的开水壶,冲炼乳自然得一次一次生炉子烧开水,所以
在当初那两年间,我奶奶是很够瞧的了,这麻烦一直继续到我四岁断了奶为止。
最早这一段事情我所知甚少,我的叙述应由我最初的记忆开始,不过这也不很
清楚了。我只记得屋里很黑,我耐心地躺在床上假装睡着,我妈用着鼻音很重的声
音哼着不成调的曲子,一边用手拍着我弟弟。她哼着哼着,没有声音了,屋里静得
只有均匀安宁的鼻息声。就在这时候我轻轻溜下眠床,蹑手蹑脚摸黑打开门溜进奶
奶屋里。奶奶显然吓了一跳,但她没有责备我。我告诉她我妈屋里尿味很重,我睡
不好。奶奶叹了一口气,便让我和往常一样在她旁边睡。
不一会,我妈找过来。
“我知道他准溜回你屋里来了,除开你这里,他什么地方都睡不安稳的。”我
听见妈和奶奶这样说,然后叫我的名字:“阿和,阿和。”
我不应,不动。
“大概睡着了。”这是奶奶的声音。
“我怕他在装蒜呢,哪有睡得这样快的!”妈又说,然后又再叫我,并摇着我
的身子:“阿和,阿和。”
我仍然不应,也不动。
“算了!”奶奶说,“就由他在这里睡吧。”
“你身体不好呢,哪受得起他吵闹!”妈歉疚地说。
这时我觉得不能不说话了,于是便说:“我不吵奶奶。”
我听见妈和奶奶都笑了,再一会,我妈就走了。
我就这样跟上了我奶奶,一直到成年在外面流浪为止;在我的生命史上,她是
我最亲近最依恋的人,其次才轮到我的父母兄弟。我对她的爱几乎是独占的,即使
她自己亲生的两个姑姑都没有我分得多。
三
但直到这时为止,我还不知道我奶奶是“假黎婆。”
有一天,妈和街坊的女人聊天,忽然有一句话吹进我的耳朵。这是妈说的:
“假黎是不知年纪的,他们只知道芒果开花又过了一年了。”这句话特别引起我注
意,因为我觉得它好像是说我奶奶,但我也不知道是否一定这样,所以当我看见奶
奶时便问她是不是假黎。
“不是吧?”我半信半疑地问。
“你怎么觉得不是呢!”奶奶笑眯眯地说,眉宇之间闪着慈爱的温馨、柔软的
光辉。她把右手伸给我看,说道:“你看你妈有这样的刺花吗?”
这刺花我是早就知道的,却不知道它另有意义,这意义到此时才算明白。虽然
如此,我仍分不出奶奶是不是假黎。我看看她的脸孔,又看看她身上穿的长衫。她
的脸是笑着的;她的长衫是我自有知觉以来就看见她穿在身上的。我觉得我有些迷
糊了。
“你知道奶奶是假黎。”奶奶攀着我的下颔让我看她的脸,“还喜欢奶奶吗?”
显然,奶奶自身并不曾对此事烦心,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好的。
我扑进奶奶怀中,说:“我喜欢奶奶。”
“对喽!”奶奶摸着我的头,“这才是奶奶的小狗古呢!”
“小狗古”是奶奶给我取的绰号。
奶奶的娘家,我知道有两个哥哥,一个已死了,留下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弟弟。
这个弟弟少时曾在我家饲牛数年,因而说得一口好客家话;而且他的脸孔诚实和气,
缺少山地人那份慓悍勇猛之相,所以倘不是他腰间系方“孤拔”,头上缠着头布,
我是不会知道他是假黎的。我和他混得特别熟,特别好。
当他们来看奶奶时,我发觉奶奶对他们好像很不放心,处处小心关照;吃饭时
不让他们喝太多的酒,不让他们随便乱走,晚上便在自己屋里地面上铺上草席让他
们在那上面睡。显然可以看出奶奶处理这些的苦心和焦躁;她要设法把它处理得无
过无不及,不亢又不卑,才算称心合意。有一次他们要走时家里给了他们一包盐和
一斗米。奶奶让他们带走那包盐,却把那斗米留下来。过后我有机会问到这件事时,
奶奶带着苦恼的表情看了我好大一刻,似乎不高兴我提出这个问题,然后问我当我
舅舅来时我妈给不给他们东西?
“虽然他们是假黎,”奶奶以更少凄楚更多悲愤的口气说,“可不是要饭的呢!”
又有一次,她弟弟夫妇俩和她侄子来看她,恰好那天是过节的日子,大概是端
午节吧?那晚上家人没有遵照奶奶的吩咐,让他们尽量喝酒,结果年轻侄子喝得酩
酊大醉,不肯老实坐着,到处乱闯,嘴里噜苏,又不知怎么砸了个碗。他叔叔两手
捉住他,把他硬拖进奶奶房里。
我奶奶气得流泪,也不说话,拿起一只网袋——我想是她侄子的——扔在年轻
人的面前,一面连连低低但清清楚楚地嚷着说:“黑马驴!黑马驴!”
“婶儿,婶儿,”我妈跟进屋里来苦苦劝解,“是我们给他喝的;过节啦,多
喝点没有什么关系!天黑啦,明天再让他走吧!”
经过一番解劝,奶奶总算不再说什么了,但仍静静地流泪。
第二天我醒来时,发觉年轻人不见了。趁着奶奶不在房里时,我悄悄地问那位
弟弟他到哪里去了。
“走啦。”他低低地说,仿佛这屋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睡着,他怕惊醒它。
“几时?”我又问。
“昨晚上。”
我不禁吃了一惊。不过我的吃惊与其说是为了年轻人倒不如说是为了奶奶,我
从未看过她生这样大的气,但就在此时他轻轻地碰了我一下臂肘——我听见奶奶的
脚步声走来了。
“不要提他。”这位弟弟摇摇头更低地说。
四
有一次,我大概是中暑,有三天三夜神志昏迷不清,大家都认为我完了,要把
我移到地下,但奶奶不肯,她坚持我会好,据说她好像很有把握。一直到现在我都
觉得奇怪,我奶奶在这上面有时有极正确、极可贵的判断,好像她看得清生死的分
际。我想这是不是和她那人种的生活经验有关呢?
果然,在她日夜尽心看护之下,我在第四天下午终于复苏过来了。后来她告诉
我,她的弟弟——不是现在这个,那已经死了——曾一连串躺了五天五夜水米不进,
后来还是好了;她说她看我和她弟弟的病一样。她以为一个人既然这样还没死,可
见他是不会死的。这似乎是她的信念。
那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开始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半天里飘,身子没有着落。忽然
我听见有一种声音,它似乎来自下方的地面,也似乎很远很远。渐渐地,这声音越
来越清楚了,好像已接近地面。这声音我觉得很熟,后来我便听出这是奶奶的声音:
她在唱歌,唱番曲。
这时我觉得我已经落到地面,觉得有东西包围着我,我有了重量;我感觉到我
的身子,我的手和脚,我的头有多么笨重,连我的眼皮都重到无法睁开。我用尽气
力,好容易才打开这重量垂合的眼皮,于是我发觉我是躺在床上的,屋里光线昏暗,
我的眼睛接触到灰白色的眠帐顶。
就在此时,歌声戛然而止,同时奶奶也投进了我的视线。
“阿和,”奶奶惊喜万状,那声音有些颤抖,“阿和,你醒了,噢!”
“奶奶!”我喊得有气无力。
我慢慢转动我的脑袋,然后我的视线停止在她的手上。
“奶奶,你——”我注视了一会之后说,但一阵晕眩使我赶快闭上眼睛。不过
我是高兴的,我好像还咧嘴笑了一下。
“你看!”奶奶把手里的东西举到我更容易看的地点。
那是用苧子挼的一团细绳,是我放纸鹞用的,缠在一支筷子上。过去我时时缠
着要她给我挼,但她事情多,挼一次只有一点点,有时则敷衍了事,因此每年我的
纸鹞都不能放得很高。现在,它已把那支筷子缠得鼓鼓的,我想一定挼得不少了。
“阿和,你赶快好,奶奶还要挼,”她笑勃勃地说,“你今年的纸鹞一定会飞
得很高。”
我的大姑姑由她那张床走到我床头来,站在奶奶后面。
“你奶奶挼了三天三夜的绳子啦,”她故意说得很诙谐,但我听得出她也一样
高兴的,“你在床上躺着,她就在你脚边挼绳子,她很卖劲呢。”然后转向她母亲,
“现在你去睡吧,我来代你。”
“还不累呢,”奶奶说。
“好啦!好啦!”姑姑说,“别累出病来啦,你的小狗古还要你挼绳子呢!”
奶奶朝她的女儿眨了眨眼,想了一会儿,好像她还不知道应不应该去睡,不过
终于还是去睡了。我看她的眼睛四周有一圈黑圈。眼睛有一些红丝。
“那么,”奶奶对我笑了笑,“阿和,奶奶去躺一会。”
“你奶奶熬了三夜了,”奶奶走后姑姑说道,“她只要自己看着你。”
这时我妈自外面进来了。
五
有一次,我二姑丢了一条牛,第二天奶奶领着我往山谷帮忙找牛去了。时在夏
末秋初,天高气爽,树上蓄着深藏的宁静和温馨,山野牵着淡淡的紫烟。我们越过
“番界”深进山腹。我们时而探入幽谷,时而登上山巅,虽然都是些小山,但我已
觉得够高了。由那上面看下来,河流山野都瞭如指掌。
我头一次进到如此深地和高山,我非常高兴,时时扬起我的手。
我奶奶对这些地方似乎很熟,仿佛昨天才来过;对那深幽壮伟的山谷似乎一点
不觉得希罕和惊惧,也不在乎爬山。登上山顶时她问我是不是很高兴,然后指着北
方一角山坳对我说,她的娘家就在那里,以后她要带我去她的娘家。
那是一个阴暗的山坳,有一朵云轻飘飘地挂在那上面,除此之外我什么都没有
看见。
奶奶时时低低地唱着番曲,这曲子柔婉、热情、新奇,它和别的人们唱的都不
同。她一边唱着,一边矫健地迈着步子;她的脸孔有一种迷人的光彩,眼睛栩栩地
转动着,周身流露出一种轻快的活力。我觉得她比平日年轻得多了。
她的歌声越唱越高,虽然还不能说是大声,那里面充满着一个人内心的喜悦和
热情,好像有一种长久睡着的东西,突然带着欢欣的感情在里面苏醒过来了。有时
她会忽然停下来向我注视,似乎要想知道我会有什么感想。这时她总是微笑着,过
后她又继续唱下去。
唱歌时的奶奶虽是很迷人的,但我内心却感到一种迷惶,一种困扰,我好像觉
得这已不是我那原来的可亲可爱的奶奶了。我觉得自她那焕发的愉快里,不住发散
出只属于她个人的一种气体,把她整个的包裹起来,把我单独地凄冷地遗弃在外面
了。这意识使我难过,使我和她保持一段距离。有时奶奶似乎看出我的沮丧,有几
次当我们停下来休息时,她把我拉向她,诧异地也关心地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是不
是不舒服,起初我只是默不作声,后来终于熬不住内心的孤寂之感而扑向奶奶,热
情地激动地喊着说:“奶奶不要唱歌!奶奶不要唱歌!”
奶奶为我的疯狂发作而惊惶失措,一连声的问我:“怎么的啦?怎么的啦?”
她两手捧着我的头让我抬起脸孔,“你哭啦,阿和?”她看着我的眼睛吃惊地说:
“你怎么的啦?”
“奶奶不要唱歌,——”我再喊。
奶奶奇异地凝视着我,然后勉强地微笑了笑,说道:“奶奶唱歌吓坏小狗古啦!”
奶奶不再唱歌了,一直到回家为止,她缄默地沉思地走完以下的路,我觉得她
的脸孔忧郁而不快。但一回到家以后,这一切都消失了,又恢复了原来的那个奶奶;
那个宁静的、恬适的、清明的。
六
到我十三岁出外求学,毕业以后又在外面闯天下,于是要我关心的事情已多,
无形中减少了对奶奶的怀恋,而且常常几个月见不到一次面。但奶奶对我的感情依
旧不变,不!也许因为离开,格外加深了她的怀念。每当我久别回家,她便要坐在
我身旁久久看着我,有时举手自我头顶一直摸到脚跟,一边喃喃自语:“我的小狗
古大啦!我的小狗古大啦!”由她的口气和眼色,我理解她这句话是要给她自己解
释的;在她看来,这小狗古会长大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有些吃惊呢。
后来我远走海外,多年没有寄信回家。她是在光复前两年死在炮火声中的;她
在病中一直念着我的名字,弥留之际还频问家人我的信是否到了。
待我回来时,奶奶墓地上已经长满了番石榴,青草萋萋,我拈香礼拜心中感到
冷冷的悲哀。
七
哥哥说后不久,奶奶的弟弟到我家来了,但如果不是他自己自我介绍,我几乎
不认得了。这不但因为他人已老,而是他的装束和外貌已经改观;他腰间已不系
“孤拔”,而穿着一套旧日军服;头发也剪掉了,因而已不再缠头布了;头发剪得
短短,已经白了,腮帮子也因为牙齿掉落而深深陷下去;唯一不变的似乎只有他的
眼睛和脸孔的温良诚实,以及一口客家话。
我领他到奶奶墓前拈香拜了几拜。是夜我们谈到深更才睡。我发现他说话之前
总要先摇一次头,由这上面看来,似乎他的晚年过得并不怎么好。
“嗨,他不做人哪!”当我问及那位侄子时他摇摇头后这样说。他告诉我这位
侄子酗酒、嫖妓、懒惰、不务正业。据说他们那里(指山地社会)也有“不好的女
人”了呢(这应该说是娼妓吧!),这是从前没有的。
他又说他大哥只生了这一个儿子,却不想是这样子的,这已经是完了;二哥呢,
没有一个子息;他自己也只生了一个女儿——已嫁了。
“这都因为我爷爷从前砍人家的脑袋砍得太多了,所以不好呢!”他又摇摇头
后这样说道。
第二天,他要走时我们又到奶奶墓前烧了一炷香,当他默默地走在前头时,我
忽然发觉他的背脊有点伛偻,这发觉加深了我对奶奶的追思和怀恋,我觉得我已真
正失去一个我生命上最重要最亲爱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