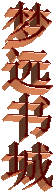
王蒙文集 心的光
这是一个美丽而安谧的小城市,它有一个简易的飞机场,砂石跑道上只能起落
四十年代出产的,“超期服役”的,那种只有一个、最多两个螺旋桨发动机的小型
客机。一出候机室,就是浓荫盖地的苹果园,青杨掩映的小路,葱郁繁茂的花草和
匆匆钉起来的木板房子……你不会相信这是八十年代的一个飞机场,你可能想到的
多半是中世纪的一个驿站。
城市里最高的建筑是五层楼房,那是一九七八年完工和交付使用的市邮电管理
局。在此之前这里的高层建筑只有三层。至今从四乡里来到这里的农牧民还在赞叹
这座邮电局大楼的崇高雄伟。城市的大小街道都铺好了柏油路,在几个十字路口又
修起了足以令北京和上海的市民羡慕的大面积的街心花园,这里的土地要比大城市
宽裕得多。平展光亮的道路两旁,是高高的白杨和长长的渠水,白杨的沙沙和渠水
的潺潺诉说着这个小城的特殊的、历久不变的魅力和新的积少成多的变化。路上有
时会飞驰过一辆上海牌小卧车,或者一辆“奔驰”,一辆“丰田”,有时甚至会有
来自自治区首府的一辆“红旗”驶过。这往往会引起一些猜测:是哪个大人物来到
了?更多的时候,道路上行驶的是运货卡车,北京牌吉普与“嘎斯六九”,是胶轮
马车、四轮马车、六根棍马车、毛驴“拉拉车”、高轮牛车。有时候还有穿戴厚重
的从山里来的哈萨克牧民骑着大马在街道上行进,他们毫不迟疑地认为柏油路面也
属于钉着铁掌的马蹄,正像服装鲜艳的各民族青年,会排成一排拉着手唱着歌儿在
大街上行进,丝毫不认为他们的走路有什么与交通规则不尽一致的地方。由于这里
车少人少,机动车线、非机动车线、人行道、人行横道等等概念不能给人们留下多
少印象;虽然在几个主要的路口设立了红、绿灯装置和交通警亭,但是,在多数情
况下,身穿白色制服的交通民警只是寂寞地注视着并不需要他的指挥,也不理会他
的指挥的牲畜和行人罢了。
在这个城市的一角,也许应该算是郊区了吧?有一个占地很大的花果园。这里
不但有品种繁多的苹果和桃、杏,而且有一个长达三十多米的大葡萄架,夏日的凉
棚。这里的花并不名贵,春天主要是金针和玫瑰,夏天主要是波斯菊,秋天主要是
玉簪和鸡冠,它们长势旺盛,三季常开,虽然需要人工的栽培,却具有一种野生的
蓬勃和粗犷。小汽车刚好可以在葡萄架下开行,从绿玛瑙似的葡萄串下面开出来以
后,便又进入了两面都是花的“花径”之中。然后,这辆车就该停在一幢被荫蔽在
树影里的二层小楼前面了。小楼有一个油漆锃亮的门脸,旋转柱式的玻璃门。在这
门脸的两边,却是两株硕大无朋的圆冠榆,榆树的一个变种,树叶又圆又大,像是
桑叶,树干又直又粗,真是榆树中的巨人。
这就是这个小城的最高级、甚至可以说是最豪华的迎宾馆。过去,只有来自北
京和自治区首府的最尊贵的客人才会被介绍住在这里;后来,又加上了外宾。而随
着经济核算的讲究,最近迎宾馆好不容易把它的门缝开得大了一点,一些来自内地
的和有身份的人,一些来自下面各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少数确与这个小城有着直
接利害关系的“实力”人物——例如决定木材分配指标的计划工作人员,也开始来
住一住了。
在这个小而佳的宾馆里,有一位与这个城市一样幽美而娴静的服务员姑娘,维
吾尔族的凯丽碧奴儿。维吾尔语里凯丽碧的意思是心,心灵,奴儿的意思是光,光
辉;她的名字的意思便是心灵的光辉,心的光。在她的浓黑而又弯曲的长眉毛下面,
是深深的两只羔羊似的柔顺而又适度地活泼的眼睛。她的眉毛是热情的,她的眼睛
却是安详的,配上她的高鼻梁,短上唇,深深的笑靥与微尖的下巴,你会觉得这确
是一个边疆小镇的天真、纯洁、有点无知,既没有充分发展也没有受到污染的大孩
子。
像本地的维吾尔姑娘一样,她的耳朵上坠着耳饰,非金非宝石却发着金子与红
宝石的光。她也有一个绣着闪光的丝线的尼龙纱中,然而,她没有像本地女人一样
地长年累月地包住头发,她的纱中多半是围在脖子上的,偶尔起了风,她也会把纱
巾移向头部,但她总要比当地女人多露出一点头发。她从今年以来有时也用一点薄
薄的脂粉,脂粉似有似无,绝不影响显露出她的真正的青春的肤色。她最近上身喜
欢穿一件褐色的尼龙绸夹克,下身有时候穿裙子,更多的时候却是穿一条灰色的毛
涤裤子。合身的衣装显示出了她的身材。说到这里也很有趣,她既不像本地妇女一
样把胸脯束得平平的,又不像自治区首府的维吾尔女人那样把胸脯耸得高高的,她
的体形线条是中庸的,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又恰到好处。至于鞋子,她坚持着这里
的古老的传统,一年四季,凡是郑重的场合,她都穿长筒近膝的皮靴,而回到家里,
她宁愿光着脚在毡毯上走来走去。
她有一个不错的家庭。父亲是民族医,精通切脉和自配药剂,他是小城的政协
委员,每年都要开两三次会,每次会后都要吃上好的包子抓饭。在她的记忆中,她
的母亲是一个美人,能歌善舞,丰腴健康,嗓音洪亮,眼睛和脖颈转动得十分灵活。
小时候她看着她的母亲觉得入迷,“如果我长大以后能成为这样就好了!”她想。
近几年母亲突然闹起病来,高血压,偏头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一下子变成了老
太婆,每天哼哼唧唧地呻吟着,使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惶恐。她们有四间带着宽大的
廊沿的向阳的房子,有半亩多果园,有一头带犊的奶牛,有七只母鸡一只公鸡,有
两头绵羊。她不知道她们还有什么应该有而没有的。
小时候她的功课很好,担任过多年的班长。他们的校长,一位跛腿的老藏书家,
曾经给童年的她讲过居里夫人的故事,希望她能成为维吾尔族的一位女科学家。初
中毕业,她才十五岁,就下乡接受再教育去了,抡砍土镘抡了四年。一九七七年,
不知道是怎样的一只幸运的鸟儿栖息在她的额头上了,她被招收到这个著名的、被
许多人羡慕和称道的迎宾馆做服务员来了。
一九七八年她曾经想报考大学。以她的基础,加上在高等院校招生中对于少数
民族学生的照顾,本来她是有把握考上的。但是她的上大学的心愿受到她母亲特别
是她姐姐的竭力反对。她的姐姐五十年代曾经被保送到北京去学习,曾经去过上海、
杭州、广州这样一些她只是在地图上看到过名字的地方。一九五八年,姐姐被分配
到南疆岳普湖工作。六一年,她由于不喜欢南疆的环境,同时,她不愿意嫁给南疆
人,又由于与领导吵架,一怒之下退职回到了小城。她嫁给了一个百货店的售货员,
开始了与这里千万妇女一样的小康的婚后生活。她很满意,丝毫也不为丢弃了学业
和工作而遗憾。她已经有了四个孩子,房屋、果园和牲畜都超过她娘家的规模。而
且,由于丈夫在商业部门,她的家往往拥有最好的物资供应。她以一种过来人的权
威口气对凯丽碧奴儿说:
“算了吧,你那个大学,我算是见识过了!每天看书呀,听课呀,做作业呀,
累得脑子疼!在大学里,没有奶茶喝,没有拉面条和抓饭,没有烤包子和油塔子,
哇呀,哇呀,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大学能赶得上我们的苹果园吗?北京,上海,有
什么了不起?那里卖的蜂蜜是褐色的,跟稀水一样;而我们这里的蜂蜜呢,雪白,
坚实,像羊尾巴上的油。还有乌鲁木齐,那里的麻雀都被煤烟熏成了黑色;而我们
的煤呢,无烟,无臭,划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着,点着以后可以封存上两天两夜不灭。
还有南疆,那里喝大渠的水,全是泥沙,人和羊睡在一间房子里。走遍天下,再没
有比我们这里更好的地方!大学毕业,也未必能找上像你现在这样称心的工作。又
干净,又轻闲,又体面,见的都是大人物,坐的是大人物才能坐得上的小汽车,吃
的是大人物才吃得上的阿克苏稻米、七五面……”
妈妈流着眼泪说,她病病歪歪,家里没人照顾。爸爸始终没有表态,他表情严
肃,深为自己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做出判断而自苦。凯丽碧奴儿是听话的,她上
大学的念头像火星一样地亮了一下,熄灭了。
宾馆的工作确实是称意的。特别是一九七九年宾馆购买了洗衣机和烘干机以后,
原来仅有的一项重活儿——洗枕巾、床单也“机械化”了,她不用担心自己的手臂
会被肥皂水泡得粗糙了,她每天的工作只是打扫卫生一次,送开水两次,和为客人
们开门若干次罢了。她和颜悦色,踏实文雅,不好奇打探,不多嘴多舌,从来不到
外面传什么哪个人物来了,哪个人物走了,哪个人物在这里购买了多少桶酥油或者
购买了多少公斤毛线之类的闲话。她也从不任意指挥首长们的司机开着高级车子为
自己服务(首长们的趾高气扬的司机都甘愿俯首帖耳地听宾馆女服务员的指挥,这
倒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所以,她愈来愈受到宾馆党支部的器重。党支部组织委员
找她谈了一次话,意在启发她争取入党,但她脑子里似乎缺少这一根弦,她从来没
有试图把自己与共产党员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称号联结起来。她没有做出应有的积
极反应,这使组织委员颇感失望。
幸福的日子就像在平原上运行着的平稳的车,你不知不觉,你以为你是处在一
种静止的、不变的、自来如此的状态之中呢,其实,你正乘着“时间”这辆车飞快
地运行。凯丽碧奴儿二十岁了,二十岁好像还没有想清楚,没有过完、过够,人家
就说你是二十一岁了,然后莫名其妙地人云亦云地你变成了二十二岁,突然,只一
眨眼的工夫,你分明知道,你已经是二十三岁了。
你愈来愈漂亮了,像一个充分成熟的苹果,闪耀着青春和生命的光彩。你有幸
生活在妇女们敢于公开地讲“美”,服装和打扮日新月异的年代。凭你的直觉,你
的衣着装束总是那么适度,既不一般,又不扎眼,你毫不费力地把继承和革新,把
民族传统与借鉴外来的形式结合起来了。
于是,在这辆平稳得像静止一样的车辆上,你运行到了对于一个姑娘来说是最
重要的一站来了。你订了婚了。被你看中了的是一位制作民族式帽子的匠人。他是
凯丽碧奴儿的小学同学。他有一双那样多情而俊俏的大眼睛,你偷偷地拿他和宾馆
的服务员们最津津乐道的一些电影演员比较(她们手里有许多著名演员的照片),
你觉得他既像达式常又像高飞,比达式常和高飞还多一层维吾尔青年的顽皮和活泼。
虽然家里有人认为他的职业与凯丽碧奴儿不能般配,但是凯丽碧奴儿还是选定了他。
除了他她再不想嫁别的人。而且他是那样主动地、热烈地追求了凯丽碧奴儿。他给
凯丽碧奴儿写的信里经常用歪七扭八的字引用这个地区流行的,比这里的特产——
蜂蜜还要甜蜜的情歌。凯丽碧奴儿为他的文化不高而羞愧,而暗暗地流泪,又为他
的热情,他的美貌,他的那些没完没了的情歌里的温暖人、融化人的诗句而动情。
他非常慷慨地给凯丽碧奴儿的双亲、姐姐和幼弟送了许多礼物。这种帽子工匠本来
就很善于赚钱。情歌加礼物扫清了他们的爱情的道路,他们和双方家长已经商定,
到秋天的古尔邦节,他们就结婚。
她等待着十月中旬的这一天的到来。她等待着她将拥有的自己的房屋,自己的
廊子,自己的苹果树和玫瑰。她已经看过新郎准备好的房屋了,用牛粪和的泥,抹
得细细的,光光的。请俄罗斯族女工把室内四壁刷成了淡蓝色。过冬用的洋铁皮炉
子已经准备好了,炉子擦得干干净净,像镜子一样,能照见自己的脸。对于她来说,
这两间没有上顶棚的、裸露着椽、檩和苇席的房子,比辉煌气派的宾馆还要美好得
多。宾馆的石柱、玻璃门和雕花门窗,已经引不起她多看一眼的兴趣了。万事如意,
她一想起便觉得如醉如酥。但一切都太顺利,太容易了,她的少女时期就这样不知
不觉地结束了,她似乎不无怅惘。
七月二十四日清晨,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旅客。他看样子三十多岁,在这个宾
馆的客人们当中,他当然算是很年轻的小伙子了。他个头不高,肩膀很宽,头发留
得很长,脸色黑红,目光灼灼,但又显得很有一些疲倦。除了他提着一个大红色的、
状如圆柱的显然是外国货的旅行包以外,他再没有引人注意之处,他这样年轻,脸
又黑,又是自己走来的(没有高级或者哪怕不高级的小车送他),所以理所当然地
被开票的人分到了全宾馆条件最差的一个房间里。他把“票”交给凯丽碧奴儿的时
候好像一眼发现了什么,盯住凯丽碧奴儿上下打量起来。这种不礼貌的盯视引起了
凯丽碧奴儿的不快,同时她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是一个级别地位都相当低的客人。她
克制地、顺从地拿起房门钥匙去为客人打开房门,她感到客人的眼光始终停在她的
身上。门打开了,客人根本不注意屋里的潮气,软床的倾斜与弹簧的突起,他仍然
在看着凯丽碧奴儿,他问:“你是这里的服务员?”
没用的话!凯丽碧奴儿心里想。她只把头似动非动地点了一下,便伸手去桌子
上取暖水瓶——给新开的房间的空水瓶灌上开水,这是她的职责。
“这里可真安静呀!”来的客人又说。
又有什么安静的呢?这儿有鸡叫,狗叫,树叶哗哗地响。拧开水龙头也会有哗
哗的水声。有汽车发动机和鸣笛的声音。每星期有两天可以听见飞机的嗡嗡声。还
有各种人声,各民族语言的交谈声,笑声。春天有各式各样的乌叫。夏天有时候有
癞蛤蟆的摇摇曳曳的啼声。秋天有蟋蟀、金钟儿。冬天的风吹着雪花呼呼地旋转。
有时候还能听到柴火爆裂和煤炭开花的音响。这不是吗,还有像他一样的客人的唠
叨。值夜班的时候才有意思呢,有的客人扯起呼噜来就像打雷——真怕它把宾馆小
楼震塌了呢。
凯丽碧奴儿就这样想着提着暖水瓶从锅炉房回转来了。奇怪的是这位客人既没
有像一般的新到来的客人那样收拾自己的东西,也没有打好一盆温热的水洗脸,也
没有拿起衣刷走到前廊上去清扫衣服上的尘土。他的红红的提包仍然斜放在地板上。
而他好像练功一样地,屁股沾着床沿儿,两腿分开,两手扶在膝盖上,两眼发直,
呆呆地坐着。
“奇怪,这儿还能听到狗叫。”不知他是自言自语还是对凯丽碧奴儿说话。
狗叫又有什么奇怪的呢?狗不叫,成了哑巴,那不才奇怪吗?你说这话,不才
奇怪吗?
于是她含而不露地一笑。笑容表达了她的礼貌,也表达了她的宽容,甚至可以
说是怜悯。有什么办法呢?来了一位神经不大健全的客人。四年了,有什么样的客
人没有来过,又有什么样的客人没有走掉,从此就消失了他们的踪影了呢?有什么
样的客人会真正引起凯丽碧奴儿的注意呢?
但是,这位客人却实在非同一般。第二天,虽然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九点
半(当地时间七点半。这是一个远离北京的地方,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实际上这
里的习惯是不会有人这么早就开始自己的工作或其他活动的。这时,文工团的红里
透紫的新星帕蒂古丽来了。帕蒂古丽能歌善舞,又会纯熟地运用维吾尔、哈萨克和
汉三种语言演戏,已经使不但这里、而且全新疆的观众为之倾倒。这一天她穿着民
族盛妆,头上戴着喀什噶尔出产的绣花小帽,耳朵上坠着真正印度产的红宝石(这
里的自由市场上要卖上千块钱一对的),以一种令凯丽碧奴儿头晕目眩的光辉来到
了宾馆。奇怪,她并没有上二楼去拜访住在特级房间的自治区首长,却径自去找那
位其貌不扬的、神经可能不大健全的客人。凯丽碧奴儿去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她以
一种明显的诚惶诚恐的、讨好的态度同那位年轻的客人说着话,年轻的客人微皱着
眉,脸部没有什么表情。过了一会儿,在服务室里闲坐着编织的时候,凯丽碧奴儿
听到帕蒂古丽竟在那客人的房间里唱起了歌儿来,那是凯丽碧奴儿最熟悉的一首民
歌:《黑黑的羊眼睛》(这里习惯于用绵羊的眼睛来形容美女的大眼睛)。又过了
一会儿,她听到了帕蒂古丽大声说话,像是演戏一样的声音。真是发了疯了,她想,
怎么大清早又唱又叫了起来,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莫非他们喝了酒?住在这个宾
馆里总应该声音放小一点,大喊大叫的客人未免太没有文明,太不礼貌,或者像汉
族同志爱说的那样——太不自觉。
帕蒂古丽走了以后,来了一位金发的塔塔尔族少女,她同样地在这位年轻的客
人的房间里又唱又喊叫,使凯丽碧奴儿犹豫了半天:该不该提醒他们放低一点声音。
塔塔尔族少女走了以后又是乌兹别克族的一位弹唱的能手。这些都是当地令凯丽碧
奴儿仰视的一些著名的美貌女子。她真不明白了,这位客人究竟有什么样的法力,
使全城最漂亮的姑娘和妇人一个又一个地来找他,像觐见什么大人物一样。中午吃
饭的时候,她听到宾馆的会计、耳目灵通的李大姐说,那位年轻的客人来自关内的
一个大电影厂,李大姐分析说,那人来到这里和一些专业、业余的艺术家接触,大
概要拍一部影片。凯丽碧奴儿正津津有味地听着李大姐的“新闻公报”,她的未婚
夫来了电话。未婚夫要她下午早一点下班,到百货商店去。“有一种新式的进口衣
料,是日本货。我想再给你做一套衣服。”未婚夫在电话里说,他的声音像奶油一
样润滑。“嗯。”凯丽碧奴儿的回答只是一个“嗯”,她既觉得幸福,又觉得羞涩,
又很好奇,那新式的日本衣料究竟是什么样子?难道除了哗叽、涤纶、快巴……以
外,又出了什么新品种了么?现在的纺织科学技术发展得好快呀!
下午,她只盼着时间流逝得更快一些。她看到那位年轻的客人匆匆地出去了,
居然还有一辆越野小汽车来接他。七点钟,这辆小汽车开回来了,年轻的客人匆匆
地跳下了车,一脸沮丧的表情,凯丽碧奴儿立即站起身来拿起钥匙准备给这位客人
去开房门,客人却不进大门,只是在门前踱来踱去,一种相当烦躁的样子。突然,
他停住了,他用目光搜寻着什么,隔着玻璃窗,看见了凯丽碧奴儿,他的眼睛突然
一亮。他迈着大步进了门,凯丽碧奴儿已经拿着了当作响的挂在木板上的成串的钥
匙走在了通道里。
“请你等一等,服务员同志!”他叫道。
凯丽碧奴儿转过了头。
“先不忙开门,先不忙开门。来,来,让我们聊一聊,就是说,啊,谈一谈。”
那人说着,自己先走进了服务室。
凯丽碧奴儿只好回身走了回来,她回到自己的服务室,等待客人向她提出要求
或者问题。
那客人又把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凯丽碧奴儿。”她低下头,从齿缝里用很小的声音回答,“我是四号服务员!”
她大声补充说。
“你上过几年学?”那人丝毫不注意她的不愿意向一位陌生人谈论她的个人情
况的暗示,继续提问。
“初中毕业。”她皱皱眉小声回答。
“你有多大了?多少岁了?”
“二十三。”凯丽碧奴儿相信,她的回答连自己也没有听清楚。
“你喜欢唱歌跳舞吗?”
她没有回答。如果说“喜欢”,凯丽碧奴儿觉得自己谈不上喜欢,她觉得自己
不配侧身到唱歌跳舞的爱好者的行列里。如果说“不喜欢”,事实上她明明是喜欢
的。
“你喜欢看电影看话剧吗?”
她点了点头。
“你喜欢读书、读文学作品吗?”
她又没有回答。她喜欢读书。但她已经好久没有读什么书了。她没有找到什么
有意思的书。她和这里的许多人一样,从来没有买过书,不是由于贫困或者吝啬,
只是由于他们从来没有买书的习惯。
“汉文书你也读得下来吧?”那个人仍然不屈不挠地问着。
她点点头。她看了一下表,还早,离接班的人赶到(中午接完电话后她已经给
下一班的服务员送信,请求早一点来换她),她去百货商店还有半个小时。
那人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录音机。他按了一下键,里面传出了歌声。凯
丽碧奴儿来了一点兴趣,虽然录音机对于她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奇东西,但毕竟她
自己并没有拥有一台,而且,这样小的录音机就更少见。她很有兴趣地看着这个装
在黑色人造革皮套里的小盒子,有一只红眼睛在闪闪发亮,磁带在均匀地转动着。
她只顾了欣赏这台“机器”,过了将近半分钟她才听出正在放的歌儿是《黑黑的羊
眼睛》,又过了十几秒钟,她才听出来,这就是早上帕蒂古丽在他的房间里唱的。
她想起了未婚夫给她写的第一封情书,曾经引用过这首歌里的歌词,她笑了。
“你会唱这首歌吗?”
“嗯。”
“你能不能现在给我唱一遍?是这样的,我很想知道……”看到凯丽碧奴儿的
惊愕和略带愠怒的表情,他解释说,“我是一位电影导演……”
电影导演又怎么样?难道就有权命令我给你唱歌吗?凯丽碧奴儿想。
“你能不能背诵一首诗,大声朗诵一下?用维吾尔语或者汉语都可以。”
凯丽碧奴儿眼睛看向了别处,过了一会儿,为了避免过分失礼与伤害客人,她
转过目光来,小声说了一个“不”字。
“你能不能……比如说,做出一个生气的样子,或者悲伤的样子,或者特别着
急的样子来呢?”
他的话使凯丽碧奴儿更加无法理解了。她开始觉得这个人的啰嗦有点可厌,她
的目光向窗外搜寻。幸好“救命”的人来了,上夜班的服务员出现在葡萄架下面。
凯丽碧奴儿抛下这个啰哩啰嗦的客人走了出去。“他是十三号房间的。”她说,把
客人交给了前来接班的服务员,没有再看客人一眼。
在百货商店门口她见到了她的未婚夫,清洁俊秀的制帽子的工匠。商店的货物
眼看着正在一天比一天丰富起来。日本进口的所谓新式衣料却并没有使凯丽碧奴儿
感到满意,那无非是毛涤纶的一种。当未婚夫让她挑选她所喜欢的花色的时候,她
突然说:“衣料不要买那么多了……买一个录音机不好吗?”
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说完了她自己觉得很尴尬。未婚夫脸上显出
了惊奇和不快的表情,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再买一身衣料,不过几十块钱;
而买一个录音机,却要几百块钱。她的话也许被认为是婚前突然提出的经济条件,
像是一种勒索。她可不是那样的人。她的脸红了。
她买了衣料,与未婚夫告别回到自己的家,有点怏怏不乐。晚饭以后她到邻近
的一个同学家里, 借来了一个单喇叭的录音机。 她回到自己房里,悄悄唱了一遍
《黑黑的羊眼睛》。然后,她把磁带倒了回去。她按下了播音的键盘,她听到了一
个自己并不熟悉的美好的声音。“这难道是我唱的吗?”她叫了出来。分明是一个
很像她的,比她的声音更温柔、深情、委婉得多的声音。她惊奇了,她按下了红键,
大声唱起了这支歌。她不顾爸爸与妈妈的惊奇,把歌儿唱完了,再次录制了一遍。
然后,她又倒回,按下。她听到了一支真正美丽动人的歌,比帕蒂古丽唱的歌毫无
逊色,而且公正地说,是更好听一些的歌,而这歌,正是她自己唱的。
我怎么从来也不知道自己会唱歌呢?
她又听了三遍,她惊呆了。
入夜,她躺在毡子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她的耳朵里是她自己唱歌的声音。她
的眼前是那个年轻的客人的热切的、有所期待的面孔。他是导演?导演是干什么的?
不,他不是导演,导演应该是一些头发花白的、坐着上海牌小卧车前来的人。帕蒂
古丽、塔塔尔族姑娘、弹唱姑娘为什么要来找他?李大姐说他要拍一部电影,一部
弹唱歌舞的电影吗?还要做出一副悲哀的样子……
他在选演员!我怎么这样傻,他这是在选演员啊!听说过,演员就是这样选的。
这是真的么?他在考虑我?不,这不可能。电影演员也都是一些全身闪闪发光的人。
而她凯丽碧奴儿是太平凡、太平凡了。然而她是多么不耐烦啊,她的那种带答不理
的态度是多么令他失望啊!
如果他真的选上我呢?他会把我带到北京、上海去吗?我会演一个悲剧的角色,
一个善良、美丽、多灾多难的女子吗?是的,小时候看完电影,不是也曾经和女伴
们一起模仿着玩过“演电影”的游戏吗?她不是会唱许多支电影插曲吗?演一次电
影,她的生活就完全不同了,她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维吾尔女人,一个艺术家……
不。那是不可能的。她的姐姐告诉她了,生活只能是像她的那个样子。可怜的
制帽子的工匠啊!看我说到录音机的时候把你吓成了什么样子,你又给我买了一身
衣料,谢谢了……然而,为什么我不敢给那位导演唱一支歌呢?即使他并不是一位
有权威有本事的导演,即使他完全不是在挑选演员,我唱一支歌又会有什么害处呢?
我还从来没有当着人痛痛快快地、大声地、尽兴地歌唱过一次呢!我从小就被教育
要低声慢语的啊!
天亮了,她有点昏昏沉沉。喝了两大碗奶茶以后,她的自我感觉好了许多。这
个小城的奶茶呀,她已经喝了几十年了,他们已经喝了几百年了,每天都要喝两次
或者三次。她的姐姐说过,去到北京,喝不上这样的奶茶,就会头疼。结婚以后,
她要给她的丈夫精心烧奶茶,像她的妈妈烧得一样好。然后,他们会有孩子,他们
的孩子又会喝同样的奶茶,烧同样的奶茶,直到他们的孩子的孩子。他们都不会离
开这个小城,不会离开这里的苹果、蜂蜜、白杨和奶茶的。
她来到宾馆,她有心找个机会与那个自称导演的客人再谈谈,如果那人再让她
唱歌,她就唱。她唱得不错嘛。打扫卫生的时候,她第一个去打开十三号房间的门。
拧了一下门把手,推不开。原来这么早他就出去了,真忙,说不定真是个导演,他
的眼光也与一般的人不同。她拿起钥匙把门开开,提起拖把走了进去,她发现,屋
里不但没有人,连那个红色的圆柱形的提包也没有了。
她撂下拖把,去找李大姐,“十三号的客人走了么?”她问,脸上显出了不寻
常的焦急。
“是的。”李大姐回答,“他昨天晚上已经结算了房钱,说是凌晨七点钟就要
赶到飞机场去。”李大姐忙着打自己的算盘去了,没有顾上注意凯丽碧奴儿的怅然
若失的神情。
“他……没有说什么吗?”凯丽碧奴儿问。
“说什么呢?”李大姐看了凯丽碧奴儿一眼,“他说:谢谢。”
……许多个月过去了,凯丽碧奴儿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位导演。十月份,她结婚
了,婚礼体面而又热烈。有三十几个年轻人载歌载舞参加了她的婚礼。制帽匠丈夫
像婚前一样地温柔,多情,照顾她。她的房间整理得一尘不染,毡子上显出色彩鲜
艳的民族图案,抖不下一点尘土。十月底,他们在房间里安装起了洋铁炉子,炉子
和烟筒子都擦得亮亮的,亮得可以照得见人。
十一月初的一个落雪的晚上,凯丽碧奴儿下班以后在温暖的炉火边翻看一本画
报。突然,她看到一张彩色照片,照片正中站着那位自称导演的客人,左边一对外
国男女,这三个人都穿着呢大衣,样子很神气。导演的右边是一个维吾尔族姑娘,
那相貌、那神态、那身材,乍一看,她几乎认为那就是自己,过了一会儿,她才发
现,那姑娘的下巴要比她圆一些,当然,服装也不一样。
她急急忙忙地看图片下面的文字报道。报道说,中国电影导演邹润文与美国电
影导演詹姆斯正在合拍一部以新疆生活为题材的电影,而那个维吾尔姑娘,就是将
在影片中饰演主角的狄丽奴儿,狄丽奴儿是和田丝厂的一个女工,她勇敢,聪明,
肯学习,很有培养前途,使中外导演深为满意。
狄丽的意思与凯丽碧的意思差不多,也是心。可那怎么就不是我呢?那颗心怎
么就不是这颗心呢?凯丽碧奴儿不敢想下去了,生活曾经怎样向她招手,给她提供
了一种怎样奇妙和巨大的可能……而她,把这一切是这样轻易地失去了。她至少应
该试一试的……
这天晚上她落了泪,而且没有理睬她的丈夫的殷勤与温存。她的丈夫说,他托
人从山上买了一只绵羊,价格要比市价低百分之二十,羊大概一两天就会送到了。
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