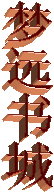
林斤澜文集 神经病
作者:林斤澜
回忆这一段生活,得说一句文话:整个儿笼罩在“历史的误会”里。
“四人帮”把我们这些做文学工作的单位,“连锅端”到农场去了。他们的居心是最坏的,要把这些事业连同个人全部报废。可是我们却怀着最好的愿望,撂下钻研大半辈子的专业,去奋不顾身的劳动,去改造世界观。
因此,这一段生活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也因此给描写带来了困难,好比这五味,以哪一味为主呢?不好调配。诸位如若感觉味儿不是味儿,只有请求原谅,请记得这是“历史的误会”。
当时农场里时兴接连排编队,吃喝拉撒睡都军事化。我们这个连队的特点是二多:老的多,神经病多。
张三、李四、王五都是神经病。张三有言无语。李四的表现是喜怒无常。王五稍稍突出一些:杂乱无章。
这三个老头子若按退休年限计算,差不多都做够了一辈子的伏案工作,也做下了一身的毛病。可是偏偏平常都不戴眼镜,说起话来偏偏都不酸,行动也都不装模作样,从来都没有犯过案子,翻过案子,反过案子……
张三年岁最长,为人最淡泊。打还没兴“靠边站”这个词儿起,他就爱靠边站。连在没边没沿的野地里,总共只有三两个人,他也总象是不在中心,在边上。怎见得呢?你看他一边儿自言自语,但见嘴唇开合,却听不见声音,但见拾根树枝或是使根手指头,在地上划来划去。除却这无声的自言自语,他的寡言水平,差不多达到无言的境界了。
李四年纪最小,嗓音洪亮,相貌粗鲁。什么干的稀的荤的素的,没有他不吃的东西。什么干净不干净,放倒头就睡。高兴起来十分健谈,凑热闹说笑话都带劲。他浑身长的是顺毛,只有几根,也许只有一根倒毛。难就难在不知长在哪里。谁要有意无意地碰着了,不容眨眼的工夫,眼面前就炸开一个雷。
王五较比出色。好比一间集体宿舍,住十个人,虽说不上窗明几净,也还利落。拨出去三个,换进一个王五,第二天,屋子就小了。锄头横在当道,雨靴站在桌面上,凳子翻过来,凳腿儿上晾毛巾……
知父莫着女。王五有个细心的女儿,送她爸爸上农场的时候,不但给整理了箱子,还描绘“图纸”一篇,贴在箱盖里面。图上表明共分三层,自左到右排列着:袜子、手套、内裤、围脖……以便为父的按图索袜等等。可是象这种繁琐哲学,从来是脱离现实的。为父的也不过索过一块手帕,绝大多数就站错了队伍。
做文章有个章法,吃饭穿衣也有一定之规。好比起床,一定,必须,不可违反地先穿袜子,再穿鞋。如果先把鞋穿上了,手里攥着袜子就不好办了,从头再脱再穿吧,外头哨子嘟嘟地吹三遍了,立刻站队跑步去了。随机应变吧。权把袜子作手套,跑出去站在斗志昂扬的队伍里。从理论上说,袜子和手套都是纺织品,都起一定的保暖作用,只不过形式上有所区别。可是“一、二、三、四”,齐步向前,紧握套着袜子的双拳,在胸前摆动。谁要说出一句神经病来,那是大家都通得过的。
你乐了吧,你那里也凑合通过了。更不用说在那“历史的误会”年头了。
话说秋高气爽,打谷场上,电转脱粒机那里,金黄的谷粒迫不及待地离开一穗穗小家当,蹦到大集体谷堆里。电动扬风机,又叫金黄谷粒经历风口浪尖,在半天空做一条金色长虹,摔掉泥土,扔掉草棍,去掉私心杂念。
连长亲临现场,他很满意。看来所有的景象,都是结合世界观的改造,热烈行进。机声隆隆,秋阳灿灿,生产和思想的双丰收在望。
场院偏西,一盘脱粒机后边,一字排开五条好汉。张三站在中间,可也侧着身子仿佛靠边。李四倒是靠边站着,可有股子一夫当关的气势。你看他头扎毛巾,肩披布褂,俨然老农打扮。稻捆在他手里,三翻两转,就褪了毛一样光溜了。连头也不回,顺手往边上一扔,背手又从身后拽过一捆来了。你看他的眼眶里,汪着往外流的劳动的喜悦。
王五没有上机子,派他在后面搬运稻捆。偏偏遇上两个胆大武艺强的车把式,竟把三马大车,刷溜溜越过复杂地形,把稻捆直接卸在机子后身c把王五间接卸在半失业状态里。
战意正浓,战斗正酣。王五岂是个袖手旁观的!他双手紧握稻捆,一跃而起。从侧面奔向机子。人家给他指了指侧面飞转的皮带轮,显然这不是正确的路线,他返回身来,从后面插上。后面站着的李四,只用鼻子吼了一声:“唔——”
显然,这里也钻不得空子。他绕过皮带轮,从机子的正前方上去。机上一字排开的五条好汉,有的用喊叫,有的用手势,有的用瞪眼都阻止不住。王五脸上积攒的情绪,已经超过了一般的严肃,可以说是劳动神圣的庄严了,战斗权利不可侵犯的威严了。他冲上去,把手里的稻捆凑到脱粒滚筒上。就象一百年前的英雄炮手,擎着火把冲上去,凑到炮筒上点燃引线了。
脱粒机隆隆地公正地转动,把张三、李四、王五的稻捆,一律打干净。事情如果到这里收场,那王五的胜利是完整的。不料这时候,他犯了人们常犯的错误。那就是胜利声中的情不自禁。王五转身扔那个打净了的稻捆时,采用了一个舞蹈动作。这个动作在舞台上是玩得转的,在场院上差点儿。当他的腰身差点儿刮着皮带轮的刹那间,有人采取紧急措施,一掌,使他倒退十来步,撞在石头堆上。这几块石头,原是随手往那一撂,准备一会儿压苦席的。经这一撞,顶上的一块出溜溜下来,直奔王五右脚的大拇哥。他穿的是塑料凉鞋,立刻,凉鞋空处,涌现生命之泉……
机子拉闸,人们两边包抄过来。一个穿高腰球鞋的赤脚医生,及时赶到。这是一位老太太,她发言的声音十分尖利,可是她包扎伤口的手段,是迅雷不及掩耳的。等连长大步走过来时,已经处理完毕,并且准确地尖声报告,没有伤筋动骨,不过大拇趾外缘,损失一块肉——35mm。
连长想找个人搀着王五回去,左右一看,立马注意到张三。因为场上所有的人,不是在行动,就是在激动。只有这个老头趁机子停转的工夫,往谷堆边上席地而坐,一根手指在谷子上画符,嘴里不出声地念着咒!连长吩咐他送王五回去休息。也快收工了,顺便到水房里点把火,温一温水。
张三去搀王五,王五岂是让人搀的角色,一瘸一拐地挣向前去了。连长一“机灵”,大声叫住他们,大声吩咐道:
“听清楚了,我是说水房里头,大铁锅下边,灶、洞、里——点一把火。绝对不是别的地方。”
回过头来,连长提出一个意见:
“你们应当阻止他上机子。”
谁知李四斩钉截铁,一口回绝:
“不能阻止。”
“?”连长脸上挂了个问号,都来不及出声。
“一个战士,抱起炸药包,去堵枪眼,能够阻止吗?一个海员去救人,往大海里跳,能够阻止吗?一个劳动者,冲向劳动岗位……”
有人说比喻不大恰当。
李四压着点嗓子,说明他同意那句名言:比喻总是跛脚的。接着敞开坦荡的胸怀,用出自丹田的声量,请大家回想王五当时的表情,那热血的沸腾,那斗志的昂扬……
这工夫,王五和张三回到了驻地。两人走过宿舍门口,连看都没往里看一眼,直奔水房。那里并排三口铁锅,研究了一下,找出那口最大的。张三蹲到灶洞口上点火,王五坐在柴草堆上管递柴草。这事也不那么容易,柴草不大干不爱着。好容易着了,续少了一着就光,续多了黄烟滚滚。几番努力,到底把灶洞烧红了,有了火底了,事情也就从容了……
这时,黄昏悄悄到来,秋风也悄悄地呜呜起来了。门外不知来了个谁,影绰绰地在磨石上磨镰刀。这秋天的黄昏,这闪闪地灶火,这嗞嗞的磨刀声,还有那屋外的风,屋里的蒸汽……好象什么诗里词里,读过背过的田园风味,好象什么小说里赞赏过的情景。那著名的“黄粱梦”,那旅店,那黄昏,那风尘,那黄粱之炊,那人生之梦……
在不熟悉的集体生活里,不习惯的劳动里,忽然得到这片刻的,熟悉的习惯的宁静,仿佛揉得皱巴巴的心灵,叫一个熨斗熨了一熨。
从早起,没有说过一句整话的张三,这时感叹道:“天有不测风云。”然后看看王五的右脚,那包扎成球的大拇哥,省略掉下边一句:“人有旦夕祸福。”
王五歪在柴草堆上,脸泛红光,浑身舒展,笑吟吟地说道:
“坏事变好事。我一生都是这样。”
张三往灶洞里添一把柴。王五映着火光,跟三杯下肚那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起一个故事。这故事要是一五一十记录下来,只怕还得说是杂乱无章。现在摘要如下:
王五出身清寒,家住沿海的一个城市。青年时一边攻书,一边在一个洋行里抄写。遇上经济不景气,到处裁员紧缩开支。一天王五走出洋行大门,骑上车,赶往学校。洋行的经理是个洋人,洋人有个杂种儿子。拿了一支鸟枪,在马路边上练枪法。把飞驰而过的王五,当做飞过的大鸟,瞄准一枪,正中左腿。王五翻身落车,后来是抬进医院。第二天,洋人看着裁减人员的名单,顺手把王五的名字划掉了。这才能够攻完他的书,得到一纸文凭。
王五说完故事的主要情节,还没有来得及总结两句,只听得门外那磨刀的,把镰刀往磨石上一拍,两步走了进来,手里镰刀锃亮,脸上筋肉横涨,喝道:“可耻!”
这是李四。李四斜眼一看灶火光影里,蜷着两个松老头,不由得降低一个调门,说:
“不要随便引用坏事变好事。”
那两个老头凭白遇上这么大份量,作声不得。李四又降低一个调门:
“那是帝国主义的迫害嘛,你怎么不气愤!”
漫漫的蒸汽,只怕也起了点作用。李四的调门,降到柔和的程度,还带着明显的惋惜,说:
“你这个故事,要是落到契诃夫手里,就是一个漂亮的短篇:半殖民地小人物的悲喜剧。”
王五这时挪过身来,一把抓住张三的手腕子,好象抓住了扒手。其实张三那只手,不过又在柴草上划拉着。王五叫道:
“刚才你写了个英文‘亲爱的’。”
张三不响,李四说道:
“那是契诃夫的一篇杰作。”
“后来你又写了俄文‘亲爱的’,后来又写了个什么文,我认不得。”
张三无言。李四感叹道:
“这一篇有的译作‘亲爱的’,有的译作‘宝贝儿’,有的只择一个字‘她’。”
李四胸中的文学、要是尽情抒发,就如海洋。可是王五还抓着张三的手腕子呢,问道:
“为什么你用左手划字?”
“右手不行了。写上两百个字,就控不住笔了。人到时候了。”
“到时候了,为什么还练左手?为什么一个字还练几种文?”
“到时候了。丢一个字,就找不回来了。”
“到时候了还找它干什么?”
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这个“无言”的张三,却是个死练多国语言的。这个“靠边”的张三,在自己的专业里边,却是个死不罢休的。李四也转过来追问道:
“到老守住一种文字还不行啊?”
张三没了法,没法之中还想把话题岔开:
“劳动还是好,锻炼了几个月,现在右手写五百个字,也还像个字儿。”
李四琢磨着,忽然单刀直入:
“你一定是有本书还没有写完。”
张三没什么表示。
“写了几年了?”
张三扭头望着灶洞里的火光。
“几年了呀?”
张三用比自言自语略大点的声音,说:
“从攒材料起,有二三十年了吧。”
“什么内容的?”
“语言比较方面的。”
“有用处吗?”
李四步步逼近,把那样沉静的老头子也逼得一跳,随后低下头,说:“不知道。”
那两个都叫起来:
“不知道你还写它?”
“怎么能不知道呢?”
张三抬起点头,望望那二位,用接近告饶的口气,说:
“在国内,”低下了头,“就我见到的范围,”认错似的,“还没有过这么本书。”
“写吧!写吧!写吧……”李四找不着别的词儿,只是从丹田里连连吐出“写吧”两个字。过后又长叹一般说道:“我们都有一首天鹅之歌,天鹅之歌,天鹅之歌……”
这“天鹅之歌”,原是外国传说,意思是天鹅临死时,都要在天空大叫三声,方肯死去。
王五也叹了口气,安慰张三道:
“再劳动劳动,右手能写一千个字,左右手倒着写。这是劳动的好处……”
李四不同意王五把劳动意义说得这么具体而微。哼了一声,斜眼扫了下王五的右脚,正色说道:
“你那个脚趾头,也有什么好处了?”
不料王五得意一笑:
“当然是有,我的一生都是坏事变……”想起李四的脾气改口说:“逢凶化吉。”
“你就说脚趾头吧。”
“那里长着个鸡眼,正好连根砸掉。”
这个意外的好处,照李四说,连契诃夫也难得编出来的。那样不言不笑的张三,竟也笑得歪在柴草上直抹眼泪水。这里王五还在补充:什么半个月要是不修脚,走不了道。什么一休假,头件事是上澡堂……这回一砸,好处可大了。
连长走了进来,说:“你们三个都在这儿,正好。”三个老头知道有正事了,立刻坐端正了。
“有新任务。”连长停顿一下,表示严肃:
“秋收时候,要提高警惕。连里研究,你们三个打明天起,白天休息,晚上值夜班。也就是按钟点儿围着宿舍转转。”
“光转转?”
“白天也睡不了一天觉呀?”
“老人觉少?”
连长有思想准备,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总还要给添点儿饶头。可又没找好合适的,试试看,就说:“劳动任务越紧张,越要抓好宣传工作不是?”
这回停顿的时间更长一点,表示更加严肃。
“我听听地头编的快板顺口溜什么的,意义很好。可有的不那么合辙押韵。不是有常用字吗?大方向,不迷航,心向党……”
“那是江阳辙。”
“对,对,江阳辙。江阳辙常用不是?斗志昂扬,改造思想,火海刀山……”
“不对,山是言前辙。”
“对,对,言前辙。言前辙不也有常用字儿?越是艰险越向前,万里征途望无边,人民江山万万年,得了,你们三位,把这些常用的字,往一块儿组织组织。”
连长没想到,立刻引起来一番议论。什么江南人,言前江阳不分。北方人又缺这短那。十三辙是由哪儿来的。还有什么辙跟什么辙乱了,还不算乱……说到热闹处,都分不清张三、李四、王五了。
连长心想:我这灵机一动,没准儿还闹对付了呢?就悄悄溜走。一边还想:也还要分析分析,从改造世界观来说,还不知走的哪一经哩?上头会有什么看法?会不会挨批?不觉犯了愁,脑袋上仿佛顶了个火盆……因此,忘了交代时间、规格、注意事项等等。
头天晚上,有人起夜,看见拐角那里,有一道光,不象灯光,也不象火光。悄悄走近几步,只见一个人坐在马扎上,两腿紧并,弯腰曲背,一手打着电棒,一手在膝盖头划拉。风寒霜冷,都和他无关。仔细一看,原来是老头张三。心想:他呀,白天还没划拉够呀。就管自上厕所去了。
第二天晌午,同宿舍的人总没见王五。他那铺上,鼓鼓囊囊,蒙着一条床单。掀开一角看看:玻璃瓶,铁盒子,手电棒,漱口杯……也不知道这一天一宿没躺下来过,还是也躺下练过一阵全身铁砂功了。
当天后半夜,黎明在望的时候,宿舍里的人被一阵狗叫惊醒,越叫越激烈,从小刀划玻璃那样的超高音,到受潮爆竹那样的泄低音,总有十来只狗,没命的喊叫,这中间还穿插几个人的紧急呼声。有人起来看看,发现宿舍不远的大道上,狗们围攻我们的老头。
是谁?怎么招来这么些公狗、母狗、大狗、小狗?说法不一,每个说法又都不容易取得旁证。事情一牵扯到王五,一般的逻辑就不够用了。再搭上张三的不言语,李四呢,你那逻辑算老几?
只好暂且不表,单说明现场情况。
张三不消说是靠边的,不过这回过了点边,已经站在沟里。他在沟里是什么姿态?不紧不慢,拾起一张张失散的小纸头。好像排炮轰鸣,对他的耳膜也不过是一阵风过。
王五操一条秫秸,又拾石头作辅助武器。可是他只有两只手,还要不住地捡那东零西落的小纸头。因此丢下这个拾起那个,拾起丢下,该丢的拾了,该拾的丢了,忙得不可开交。
只有李四,站在风暴中心。手握一叠纸头全无失落。两脚站定,寸步不让。面对群狗,厉声斥责。有几条滑头的,绕到他背后来吼叫,他理也不理。仿佛从背后上的,连狗也不是。倒没有一条狗,敢咬他的脚后跟。
等到大家过来,狗们也就一声不响落荒而走。大家动手抬纸片,抬回来灯下一看,不得了,这三个老头,把一部《新华字典》,据说八千五百三十六个字,挨个儿排了排队。共分十三个连,江阳、言前、发花……每个连又分四个排,那是平、上、去、人。
看看那些字,有言无语张三,写得秀丽如刺绣。喜怒无常李四,字如其人,奔放不羁。可是那严谨工整,一笔不苟的,倒又出自杂乱无章王五之手!
这些小纸片订成本子,成了我们连队的队宝。每当节日编排节目,就有别的连队走来借用。听反映,有说是两天工夫弄出这么个宝贝,一般人是办不到的,除非是神经病!
到了春节,这个小本子该当派大用场的时候,却谁也摸不着了,我们连长给收起来了。走去问连长,他总是摇摇头,摆摆手。
对了,说了半天,还没有把我们的连长具体介绍一下,他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知识分子。人家可是贫农出身,解放才上的学,后来到了我们的单位,好象野地里一颗小树,给移植到书香的四合院里。他老剃个小平头,穿双老布鞋,大手大脚,说话迟慢,很有股子粘糊劲儿,粗活细活都给悄默声地做了。他自己说马列水平不高,文化水平也差劲,就是知道与人为善。
过不几天,听说什么“复辟”啦,什么“黑线回潮”啦,又要批斗,又要抓后台。我们连里暂时没有动静,因为连长病了,白天脑袋痛,夜里说胡话。人说我们连没有好人了,连长也得了神经病。
要以为我们听见神经病就难受,那也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在那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的时候,“神经病”属于酸甜酸甜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