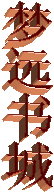
林斤澜文集 假小子
作者:林斤澜
火车站
山重山,火车在山肚子里钻来钻去。车头钻进这边的山腰,车尾刚出那边的洞子,好像海洋里的一条龙,使一个猛子,探出头来吸口气。山高天低,黑烟和白云戏耍。四山轰隆轰隆的响声,就跟上天下地滚着的一般。这光景雄壮极了。
这么个山坳里,有一个三间屋的火车站。原本也许有十来家人家,可是那一间屋的饭铺,那两间屋的百货商店,那工棚似的诊疗所,那亭子一般的邮电局,想必是随着火车站,才办起来的吧。
过了晌午,山沟里一阵风过,暑热就消散了。新来的老站长,走到门前的柳树下边乘风凉。他在树根上坐得稳稳的,把一杯酽茶,放在石头礅子上。有几只雪白的来亨鸡,在脚边盘来盘去。老站长虽说头发花白了,可是脸上油光油光,老有一个老年人的和气的安静的微笑。
树下,还有几个等车的旅客,人数不多,可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看那衣着,那在自己家里一般的神色,就知道都是身边四山的乡亲。有人跟老站长打了个招呼,说:
“山坳子里好不好?过不过得惯?”
站长望着来亨鸡,微笑着,和和气气地应道:
“好,好,过得惯,好。”
乡亲们,厚道的山里人,都象委屈了老站长似的,一个个说道:
“上坡下坎的,走动不便。”
“吃没好吃的,瞧没好瞧的。”
“人呢,都是大老粗。”
老站长抬起头来,略一寻思,说:
“有那么个人,这两天又不见了……,前天,我刚来,站里开过饭了。我上那小饭铺吃点儿去,正赶上一伙赶车的客人,急着等饭吃。一个上年纪的服务员,拿汤端菜,忙得团团转。我心想,走吧,待会儿再来吧。忽听见一个大嗓门,嚷着‘得罗,得罗’,只见一个留分头的后生,穿着大垮垮的白褂子,高高捧着个托盘,托盘里饭碗菜碟,都堆尖地摞起来了。他几个大步,一个转身,客人们面前就都有了饭啦。好利落的服务员。可我细细一看,那后生白白净净,透着秀气。身上圆滚滚,嗓门大是大,可又带着点尖溜溜的,怎么倒象个姑娘呢?我吃完饭,写了封信,上邮局寄去。刚在粘邮票,听见背后登登登,一个人闯了进来,也不招呼,径直闯进柜台里边,指着这个包那个卷儿,跟邮递员嚷着,这给捎到什么村去,那是哪个队部的。不知为了句什么话,还哈哈大笑,‘嘭’地捶了下柜台。我抬头一瞧,还是那个后生,不,这下我认出来了,这下没穿那大垮垮的白褂子,才认出来是个短头发的姑娘。可又让人纳闷,她倒是饭铺的服务员呢,还是邮务员啊?我寄完信,左右遛遛,认识认识新地方,顺脚走进百货商店,看见一个老乡,捧着一双鞋。柜台后边没有人,老乡冲着里屋说:‘行了,不用试了,地里来的泥巴脚,一试还不试脏了。’只见里屋有人敞着大嗓门说:‘买鞋哪能不试试呀。’说着,登登地端着一大盆水出来了,一瞧,又是那个短头发的姑娘,她让老乡洗个脚,好试鞋。我可真纳闷,她怎么又变成售货员了呢?可是这两天,仿佛又没见她了,哪儿去了?这是谁啊?”
老站长还没有说完,乡亲们早笑开了,大家说道:
“假小子,准是假小子。”
“是她是她,她是咱们百货店的售货员,这两天准是下村子送货上门去了。”
“哪儿都有她的活,什么背角落她都钻得到。”
“连梳根辫子也嫌麻烦,一剪子给铰了。”
有一位老人家,指着脚边盘来盘去的来亨鸡,说:
“站长,春起要不是她呀,你们站上也别想吃鸡蛋罗。”
来亨鸡
说话的老人家,年纪跟站长仿佛。可是站长脸上油光光的,他却跟老树一般。站长老有个安静的微笑,他可是一说话,就舞胳臂,提高嗓门,坐也坐不稳。连同身下的石头块,往站长跟前挪了两步,他说:
“我们村里,哪家也养了十来个来亨鸡。往绿草坡上一放,瞧吧,浑身雪白,冠子血红,不比花朵好看吗?花朵是死的,这可是活泼泼的呀。每天每,还给下一个油光光的蛋儿。谁知春起,嚯,哗啦闹开了鸡瘟。吐黄水,拉稀屎,一半天工夫,我家栽倒了五只。瞧着真叫人揪心。赶这时候,假小子来了,来干什么?收购鸡蛋。我说你这收购计划,怕得打个折扣了。她说不行,国家需要。我说需要也没有法子。她扭头往鸡棚里跑,一瞧,扭回头来,嚯,举起拳头,倒象要捶我老头子两下,敞开嗓门那个嚷呀:鸡药,鸡药,鸡药。”
老人家说着,又连同石头块,往站长身边挪了挪,说:
“我知道咱们这里没有鸡药。火车才站一分钟,多少要紧的东西得往下卸。火车一身的任务,不能多站一会儿,哪里顾得上卸鸡药。可是没想到这假小子,她要起了心,山挡不住,黑夜也拦不住。她说社里许有区里也可能有,我说得了,这一来回,有也来不及了。她说抄近路,翻大梁。嚯,这大梁上下三十里呢。她扭头往山上跑,我怎么拦她呀,我说回来回来,为小鸡子不值当。嚯,她翻了我那么一眼,只顾走。我说回来回来,你不看看都是什么鸡。她边走边说,不就是来亨鸡吗。我说可不,那不是本地种,不服咱们的水土,没药治。嘱,她扭回头来,翻了我那么一眼,奔到鸡棚跟前,抓起一只病鸡,扯下围巾裹上,拎着就走,我说回来回来,给你根棍儿。她又扭头回来了,我心想,到底是姑娘家,嘴头冲,心头还是胆小啊。我给她根棍子,说,上下三十里可没有人烟。一听这说,嚯,她那么一‘机灵’,那么举了举拳头,倒象要打人了,夺了棍子,扭头又走了。”
这时,有个厚墩墩的后生,张了张嘴,还没有说出什么来,老人家叫道:
“兄弟,你等等再说。她一走,又有两只鸡蔫了,支着毛,缩着脖子,耷拉着眼皮,瞧着揪心,真揪心。心想假小子这一趟,要弄到了管事的药,那就太好了。到晚上,躺炕上也睡不着。忽听见山梁上,哇哇的,是狼叫还是人喊哪?走到外边细细一听,远远的,悠悠的,可听得出来是假小子的嗓门。万万想不到,她夜间翻大梁回来。她一路唱嚷,干么那么高兴?我一琢磨,准是给自己壮胆罗。我急了,把左邻右舍的姑娘后生,叫了起来。我领着,上梁迎她去。那晚上,有半个月亮,山梁上朦朦胧胧的。我说姑娘后生们,也唱起来吧,会什么唱什么吧,使劲地唱吧,梁上的假小子,她得钻一片树林子呢!那晚上,唱得雀、鹰、老鸦,扑楞楞往天上飞,唱得梁上梁下,四山嗡嗡的。唱得那半个月亮都发懵了。唱得心头那个欢喜呀,不唱都不成了。”
这时,那个厚墩墩的后生,小声说了一句:
“有这事。”
他不像是插嘴,也不冲着谁说。别人也没有注意,只有老站长可看在眼里了。一个妇女插上来说:
“也上我们村里去了,挨家挨户地撒药。”
那老人家这时真地坐不住了,舞着胳臂站了起来,说:
“大嫂,你先听着,我老头子还有两句。我跟假小子说,姑娘,你可帮了个大忙了。她那么翻我一眼,举了举拳头,说:‘完成国家计划,别打折扣就行了。’
“我说你别操心了,不用来回跑了。这个村里的鸡蛋,都在我老头子身上。说实在的,咱们山里人说话算话,到时候家家都把鸡蛋交给我,我整花篓地给假小子背了去。她说这可帮了个大忙了,我也那么翻一眼,那么举举拳头说:‘不打折扣完成国家计划就行了。’
“我老头子就这么句话,大嫂,你说吧。”
老人家这么一让,那位妇女倒不好意思了,扬脸望着山头,说了两句:
“我们村里没死多少鸡,可她一送药,倒把幼儿园给治了一治。”
大家不觉“哟”了一声。
幼儿园
说话的妇女三十来岁。黑红黑红。一说话,只见两行牙齿,整齐,雪白。她飞快地看了大家一眼,就转脸望住莽苍苍的山头。好像她要说的事情,正藏在树林中间,得缓缓地寻了出来。她说:
“假小子挨家挨户地送鸡药。她可不是个光跑腿的,走到哪个院子,也打听短什么,富裕什么。敢情要买的要卖的,她都给惦记着。走了几个院子,小鸡子没什么事,她倒寻出一件事来了。”
仿佛在树林中间,寻着了话头,这位妇女一变调子,飞快地说了下去。
“假小子问:‘不是春耕忙上来了吗?怎么女将们都在家?’
“‘叫这些小孽障坠住手了。’
“‘怎么不上幼儿园?’
“‘也得爱去。’
“‘怎么不爱去?’
“‘去了也爱闹小病。’
“‘怎么不跟队长提提?’
“‘提了提了,队长在研究呢。可这不是买也不是卖,你别怎么怎么的,非问到山穷水尽。’
“‘嫂子,你怎么了?我们是支援生产的,生产上什么最要紧?是人吧?我们不想方设法,让人们安心上生产前线,还怎么能叫支援?’
“假小子这就上幼儿园去了,怎么怎么地问了个山穷水尽。跑到地头,找着队长,问道:
“‘怎么不添置玩具呀?’
“‘晚上研究研究。’
“‘怎么暖和了,还不把炉灶挪到外边来?不然孩子们爱闹毛病哩!’
“‘人都忙春耕去了,回头研究研究吧。’”
这位妇女一口气说到这里,又放慢了调子,仿佛那位队长,闪到山头的树林深处去了,得缓缓地找到他。
“我们队长有年纪了,抓生产,一点也不含糊。可有一样,遇着他觉着不大要紧的事,好说研究研究,且搁在一边。谁知这假小子,等到晌午,妇女们都上食堂吃饭时,又找上队长了。”
这位妇女不觉又飞快地说了下去:
“‘队长,妈妈们都在这儿了,怎么研究呀?’
“‘嗐,这里头有个难处。’
“‘怎么个难法?’
“‘钱’。
“‘怎么就叫钱难住了?’
“‘今年不是买很多化学肥料吗?钱都花了。’
“‘怎么连个零头也拨不出来?’
“‘别着急,晚上研究研究。’
“假小子举着拳头,只听见她怎么怎么地不住嘴:
“‘怎么能让这点钱难住人了呢?让人下了地,怎么也比这钱值得多。’
“有个孩子的妈妈说:‘依着做妈妈的心哪,卖破烂也把这事办下来。’
“队长说:‘破烂不用研究。近处谁要?远处,火车才站一分钟。’
“有个妇女说:‘一家卖点菜籽儿,我瞅着都够了。’
“假小子赶紧问:‘什么菜籽,你们怎么有菜籽?’
“‘自留地上收的呗。’
“‘那怎么能卖?自己不使了?’
“‘去年收得好,谁家也使不清。’
“‘嫂子,你怎么不早说。这可不用上火车,本公社里就需要。’
“假小子说着,高高地举了举拳头——她好举拳头,那位大爷说,跟要打人似的。可我瞅着,怎么倒象敬礼那样。”
这位黑红的妇女笑了笑,两行牙齿雪亮。一个中年男人不慌不忙地说道:
“这菜籽是这么来的呀,不简单。可是嫂子,你先说完吧。”
那妇女看了大家一眼,又望住莽苍苍的山头,缓缓地说道:
“过了两天,假小子拿着一叠票子,交给队长。我们队长乐得张嘴张手,可是不接钱。说:
“‘好假小子,帮忙帮到底,钱你拿着。你做对了,让妈妈们研究去,该买什么,还是你给捎了来。最好把幼儿园倒个个儿。’
“打这起,队长走到哪儿,也夸假小子。他怎么能不夸,春耕春种上,添了二三十个妈妈下地呢。”
大家一笑。那老站长又注意到,那个厚墩墩的后生,甜甜地笑着,管自点了点头,说了句:
“有这事。”
那个刚才插了两句话的中年男人,这时站起来,不慌不忙地笑道:
“各位,好有一比,咱们这里的火车,刚由这山肚子里钻出来,立刻又钻到那山洞里去了。假小子办事,一头钻下去,一气儿解决一串。由这菜籽,她解决了水桶子水斗水车呢!”
大家不觉又“哟”了一声。
水桶子
这位中年男人的头发拔顶了,长脸,大脑门。上身穿的是中式褂子,下身是制服裤。他站在柳树下边,柳条在他的脸旁飘摇。他笑洋洋地说道:
“一个平平常常的人,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他张嘴先提出这么个问题,接着不慌不忙地挨个望望人们,看来是个山里的读书人,还是常在会场上发言的人。
“各位:这么一个山坳,自从立下火车站,才有勉强说是半条街。”他打挺老远的地方说起,“街上有那么一家两间屋子的百货商店,商店里边,柜台有新有旧,货架有高有低,就是说凑合起来的。柜台后边,站着穿家常衣服的售货员。这实在是报上常说的: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站在这岗位上,能做些什么呢?把日用百货的品种、价码、质量记得烂熟,算盘打得劈里啪啦,再加上手脚勤快,说话和气,也就算是不错了吧。可是你看假小子,柜台哪里拦得住。她起的作用,两间屋子哪里盛得下。她收了菜籽,转给缺少籽种的生产队。这事不就完了吗?不,没有完。过了些日子,趁下村送货,她惦记着上秧地里,看看菜籽的发芽率。眼见芽发得不错,嫩幼幼的一片。这不就完了吗?不,她发现人们浇水使的桶子,滴滴答答地漏水,一问,一时买不到新桶子。哟,她想起来了,快到栽白薯的时候了,白薯不是多半种在高冈地上吗?水上不去,不是得挑水点种吗?她立刻跑到队部,打听需要多少桶子。队部觉着这事可得先走一步,立刻表扬了假小子。马上去各小队调查,总共需要桶子二百挑。假小子得到了鼓励,紧跟着向商店上级反映。可是咱们国家大了,新建设多了,桶子暂时发不到这里来。这可怪不得火车,别说站一分钟,就是站上十分,也是卸不下这号货。商店跟队部一商量,想出两个办法,一个是找代用品,就是柳斗。一个是修理旧的。又作一次调查,破的漏的旧桶子,总有一百多挑。东西不少,这个修理任务,交给了假小子。这位姑娘眉头也没皱一下,拿了个介绍信,直上区里,找着黑白铁合作社。可那个社里,正压着大批的活。谁知她找党委,把咱们的情况一说,觉委就给派出一个老师傅。听说她在人家那里,也那么举了拳头的,不过这个不关紧要。商店里拾掇了一副挑子,由假小子领着这位老师傅,串小队,上门修理。各小队的队长、书记,没有一个不欢迎,不表扬的。假小子说,她不过是帮着老师傅,敲敲桶底子,可是得到的鼓励,是桶子没法量的。她更加留神百样事情了,眼见有了水桶子,可是有的水车,打水不利落。其实水车不爱坏,就是那些小零件,日子久了得换换。什么皮钱,螺丝,管子,链子,都是不好掏换的东西。假小子这回心里也没有底,可是不言声地揽了下来,上梁下山,区里社里,不掏换齐全了不撒手。跟人举没举拳头呢,那恐怕免不了,不过这个不关紧要。等到齐全了,一亮出来,可把人们吓一跳,喜欢得炸了。”
那个厚墩墩的后生,又轻轻说了句:
“有这事。”
他管自微笑,笑得那个甜法,正是如糖拌蜜,蜜里调油。都叫老站长看在眼里了。
一个瘦长个子叫道:
“修着水车,还帮我们村里搞了个柳斗组。她打七八十里地外,访到了一位技术人……”
那位中年男人不慌不忙的,截住说道:
“你看,她的事儿,一个紧跟着一个,好象一个个的山头。有一天,她翻一个大山,走得浑身火烫,走到顶上,一看,迎面陡的又是一个高峰。她望了一阵,倒好笑起来,心想:‘原来咱山里人的脾气,跟山一样。’……”
中年男人说到这里,挨个望望人们。正要把这句话,有条有理地分析一下,可惜一言未了,听见山洞里,哦哦地冲天叫喊,立刻四山轰隆轰隆,雷般滚动。洞口冒黑烟,又有两道白光闪亮。人们早已站了起来,往铁道边上走去。那位瘦长个子一边走,一边还抬高嗓子,抢着说几句话:
“我们那里,有的是柳条……可是谁也不会……你们使上柳斗没有?顶得上桶子吧?……”
只有老站长不忙,端起面前的口杯,喝了口酽茶,才背着手,拿着红绿旗,往道边走去。
假小子
老站长送走火车,回到柳树下边,却看见那厚墩墩的后生,还在那里坐着。问道:
“你不赶车?”
“不,我等个人。”
老站长又坐下来,刚要端口杯,却叫山景愣住了。只见火炎炎的一轮红日,蹲在西山头,把天边团团块块的云彩,烧得鲜红、朱红、桔红。有的镶金边,有的嵌钻石。眨眼间,这莽苍苍的山坳,仿佛投进了熔炉。老站长看得出了神,油光光的脸上,也映着火光。那个安静的笑容,也透着惊讶了。心想:好不雄壮。忽听身后有人叫道:
“过来,喂,过来。”
回头只见厚墩墩的后生,跳了起来,向铁道那边招手。那边,有人一路小跑,小马撒欢一般跑下山坡,一路哦哦地放声答应。听那嗓门,可不就是假小子吗?那后生一手拎上挎壶,一手提个包迎了前去。两人在铁道上会合了。
假小子敞着嗓门笑道:
“哈,你又在这里等我。”
后生可是小声嘟囔着:
“谁等你呀,我在这歇凉来着。”
“倒好,回头你给商店捎个信,说我上队部去了。”
“走到家门口,还不回去一下。”
“白菜长虫子了,喷雾器不够使。队部许有闲着的。”
“草帽呢?”
“丢了。”
“丢在哪儿?”
“不记得哪个村子了。”
“大太阳底下,能把草帽丢了,真是丢三落四。”
听见丢三落四这句批评,老站长很觉意外。回头一看,两个青年人,并肩坐在铁道上,遍身的红光,好像坐在红霞里边。那圆滚滚、白净净、短头发的姑娘,举起拳头,叫道:
“咱们说定了,别在这里等我。”
“谁等你——,咱们早就说定不喝生水,可你连个水壶也不带。”
“忘了。”
“丢三落四。拿去。”
后生把手里的挎壶,递给姑娘。假小子拧开盖子,仰脖子就灌。后生嘟囔道:
“这是下地喝剩的,别当我给你预备下了。”
“记住,别在这里等我。”
“没有人等你。逮住一句话,你也不撒手。”
“回去告诉商店,民兵队的胶鞋,给送到了,大小号全够了。”
“丢三落四,刚才还有个老爷子,在这里说你,翻大梁也不记得拿根棍子。”
“今晚上我要不回来,明早你提醒他们,把六六六粉赶紧往村里送去。照着单子送。”
“丢三落四,拿去。”
后生把身边的小包塞了过去。姑娘扯开一看,敞开嗓门笑道:
“哈,褂子,你在哪儿找着的?我丢在哪儿了?”
“我才不给你找呢,人家老乡巴巴地送了来的,你说你丢三落四不?”
“我走了,你回去吧。”
这时,老站长猛地站起来,紧腰带,扣领扣,一边说道:
“上队部去吗?咱们一路。”
“有事吗?”
“也没什么大事。”
“道儿不好走呢,要是不大要紧的,我给你捎个话去。”
老站长望着这位记得民兵的胶鞋,幼儿园的玩具,各村的鸡药,水桶,六六六粉,可是记不得自己的草帽,水壶,褂子,丢三落四的姑娘,十分郑重地回答道:
“不,我应该去走走。火车得走好些地方,在咱们这里,只能站一分两分钟。可是咱们会有法子,叫该上的都上得去,该下的都能卸下来。”
说着,两人上了路,姑娘忽然回身,举起拳头。老站长看着,心想说是要打人似的也行,说像个敬礼也可以的。姑娘叫道:
“别在这里等我了。”
只见那厚墩墩的后生,还在铁道上扎实站着,甜甜地笑着,如糖拌蜜,蜜里调油。
姑娘扭头走了几步,问道:
“站长,这里上坡下坎的,走不走得惯?”
老站长抬起手臂,划了个圆圈,这就指了红日,指了山头,指了云霞,树林,洞子,三间两间的房子,最后,指头落在假小子的心口,心平气和地说道:
“这里雄壮极了。”